理性·建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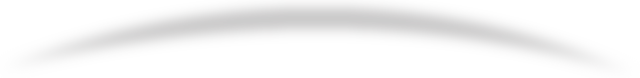


董源为南唐画院宫廷画师时,主要活动在南唐中主李璟年间,卒于后主李煜即位第二年。中主李璟,文武皆能,对外开拓用兵,后庭谈诗论画,把个南唐经营得风生水起。时血沃中原,民不聊生,董源在江南,生计优渥而稳定,因兼任北苑副使,管理皇家茶苑,人称“董北苑”。绘画之余,又添了一份赶春吃茶的风雅。但凡产好茶的地方,都有一片好山水,他一边吃茶去,一边寻山问水,这在乱世,便显得弥足珍贵,他与春天一期一会,与江山一期一会,明年江山属谁?谁知道呢。赶紧把好山好水带回家,画画吧。
淡设色的桃花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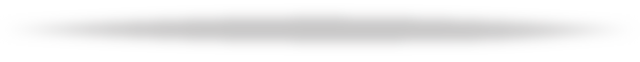
若谓荆浩在北方大山里皴染其理想国,那么董源则在江南烟渚里渲染桃花源。
后梁,盘踞太行,有背靠大山的底气;南唐,跨越长江两岸,有江河湖汊隐约扁舟垂钓的安逸以及丘陵逶迤错落耕读人家的笃定。与荆浩不同,董源不避世就已出世,至少从山水气象来看,整个南唐家国就像一座出世的仙山画卷,他不必像荆浩那样自我放逐到太行山里,他有皇家画院可去。若嫌画院烦闷,那就到茶苑去转转,他所画的丘陵绵延,确有茶林起伏的烟峦。
董源师法荆浩,除水墨技法、山水形式外,还有精神气质上的追随。他虽在皇家,但精神早已游离,是荆浩的水墨山水样式,唤醒了他的自由意志,敦促他从传统皇家金碧富丽的山水中出走,带着皇家山水的赭绿走进水墨皴染的江山情怀,一番沐浴更衣后,眼前已是一片淡设色的桃花源了。
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这样说董源:“画山水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这一评价,虽为董源山水定调,却忽略了董源在两者之间精耕的那片淡设色的过渡地带所内涵的美学张力。
王维被看作中国文人画之开山,“类王维”,是说董源已得文人画的“造意之妙”,而此“妙”是被苏东坡的审美之眼捉住的,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文人提供了“不托之诗则托之画”的精神渊薮;“着色如李思训”,则道出董源绘画的出身,还留有皇家山水遗范,院体贵格。李思训生于大唐盛世,又是宗室之嫡,他重用青绿画山水,追求色彩明亮,以其严谨恪守视觉艺术的内在法度,而不失庄严富丽,造物意境直率,直奔贵气而不妥协,笔力一分一分地为美的尊贵打分,勾勒点染出皇家金碧山水的典范。
董源的设色谱系,的确出于李思训金碧山水一脉;但荆浩的水墨山水,对他的影响不啻一场精神“诱拐”,水墨才是他的生命底色。在水墨上,施以淡淡的青绿,是一颗自由的心灵追随荆浩的笔墨意志,从皇家艺术语境的一次个性化出走,是从李思训的典范中,一次任性于艺术呼唤的自我放逐。
他走得轻声淡色,踽踽独行于水墨烟绿的平远中。对他来说,批判不是一种话语权的对峙,而是以一种更为自由的色彩驾驭能力,给予一个比金碧山水更美的呈现;在对浓设色谱系消解的淡设色中,足足过了一把自由设色之瘾。看得出他在解构既定色彩秩序中获得了欢快与巨大满足,但他内心沉淀的艺术律令,给予他的判断能力,不是基于是非好坏,而是美的法则,才会使他有以王维和李思训互为宅邸的自如,以及在院体与文人趣味之间游走的放松。他的山水,既不承载表达政治正确的金碧大青绿,亦非为高蹈之士归隐独居准备的峭壁奇瀑、或沽名钓誉的花头,而是个可隐可居可游的所在,是个渔樵耕读可以诗意栖居的桃花源。
观画如观人,正如他“不为奇峭之笔”而高扬自我,亦不为“金碧”折腰亏损自由。
就从董其昌收藏的半截《潇湘图》谈起吧,绢本,淡设色,卷长141.2厘米,纵50厘米,不施一笔水纹,却有烟波万顷的舒阔,借助绢底色反映光与水的融洽,表达云雾晦明之效。晦明,是光在空气中被水气分解后的隐约状况,是对江南烟雨的微妙写照,还真有那么点“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味道。
画面上,圆峦绵延,迤逦到湖天尽底;山脊线在“披麻皴”细腻而密集的拥趸中给出远远的天际茂密,偶尔雾霭泛涌,却带来山头呼吸光的通透。淡淡的笔墨,为山坡草地“披麻皴”出丘陵的舒展态,为山石点染圆融与错落,节奏从容而淡定。顶天高山脚下的坡地间,丛树深蔚,有茅屋两栋隐居。山坡伸向湖水,为归帆的靠岸,为旅人的作别,为红颜的折柳,为捕鱼的生计,为蓑翁避世的垂钓,那山与湖才相挽相拥,彼此契约,永不分离。
而那深入湖心的洲渚,则争相邀约两岸,却又衔水擦肩形成湖岔,隔水注目,纵横复杂,滋养着芦狄草木繁密而为鸟禽栖息的湿地。截半处的沙洲上,有数丛芦狄,萧疏若梦,恰到好处。不知被截的那一半是怎样的图景,仅此亦有不可续之美。远处散落三五渔船似柳叶御风,近处一大船,许是刚刚离岸抑或即将靠岸,可见艄公与舵公分立船头船尾,伞盖下坐紫衣白衣人,岸上数人彬彬,揖别或迎归。再远的对岸,水中岸上有十人结网,不见渊鱼却知鳜鱼正肥时。
这幅淡设色的桃花源,水墨没有横空出世的喧嚣,而是静若处子;淡绿设色,亦非外在涂抹的追求,而是持守赭绿内在生命力所支撑的端拱与体面,在笔舔“净静”中,新生出一种精神洁癖。
灵魂奔跑的山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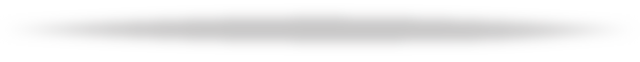
董源的山水画,内存一种救赎的力量,潜藏在“淡墨轻峦”的笔墨关系中。
造景中的远山近水之澄明,似乎可以洗涤所有穿透它的视线;江渚浩渺里,有一颗寄托了美学信仰的的心灵。山水画的对象,原本就纯粹,而董源以其天真的洞察与对象的纯粹性一拍即合,他只要尊重所要表达的对象的天性并顺从自我的天性,就足以创造一个纯粹美的世界。面对如此“净静”的世界,任何世俗的欲望都会惴惴不安。这种对人性的净化力量,出自审美的拯救。
淡设色,最适宜于江南山水的淡远,在表达与被表达的“淡境”中,淡化了人的欲望。水墨淡,青绿也淡,山不动,水也不动,一切静默如天,但它所呈现的美学意味却如同一个信仰层级的过滤器,过滤了人间所有情绪的杂质。没有任何宣喻教化等人为的企图,没有帝妃缠绵的潇湘传说,没有神人交感的暗喻,唯有恬淡。
“恬淡的富足”,是心灵的尺度,可用来衡量人的精神富裕程度,为人文精神提供一个不再拥挤的上升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文是船,是渔网,是送往迎来的山居岁月。
米芾评董源画,长叹道:“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其子米友仁也有《潇湘奇观图》传世,可见“米家云山”已得董北苑山水真髓,米友仁“自识”曰:余居镇江四十年,生平最熟潇湘奇观。
《潇湘图》不但“净静”,而且“生动”,“净静”是画面,“生动”是画面呈现的灵魂姿态,那样的天真,救赎之力浩浩荡荡。
董源的另一幅画,《北苑山水图》,卷轴,绢本设色,纵38.8厘米,横593.8厘米,上有宋御府宝藏大印以及多枚藏款钤章,并附后跋曰“当为北苑真迹”,因其笔墨,确与董源之《夏山图》、《潇湘图》“如出一手”。近6米长的卷轴上,淡设色的峰峦起伏,似山风奔跑,又从容不断。如果《潇湘图》“净静”到几乎容不下一根针的跌落,那么《北苑山水图》的山脉运动则像流浪远方的长江之水,永无休止地逐浪飞花却又波澜不惊。
两幅画,一静一动,是董源对江南山水丰富内涵的精准提炼。无论其“静如处子”,还是“动如脱兔”,皆发自他“平淡天真”的内心。他在《潇湘图》里浸淫平淡,与自然的淡定相呼应,却在观者的心灵里引起波澜;而在《北苑山水图》中,他画山丘绵亘动如脱兔奔跑,灵魂浩瀚之后,却平复了观者的心灵。
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将熟悉的对象陌生化。如果毕加索、达利算是现代的例子,那么一千多前的董源,就已经开始将他熟悉的山水陌生化,那些拉长、变形的峰峦,奔放的山脊线,画家哪里是临摹自然,他是把自然作为释放自由意志的长廊,在勾勒江南丘陵的地势中构造与人的精神关系,展示了不同于西方个人焦点透视的追问。
他暂时悬置了善恶,与他笔下奔跑的山脉一样,迫切追问人在自然中生存的审美意义以及生命应有的样态。因此,他不给你静止不动的大山,而是让你与他的山脉一起奔跑,就像夸父逐日,让你的灵魂在焦渴中获得点点皴染的宇宙意识,颠覆了传统观念,却满眼芳华。
峰峦憨稚,被山坡携着,迈向远方,山岗追随,起伏光的欢乐,草木摇曳,翻滚风的笑声。光与风,掠过林木间秀密的枝叶,吹拂草廊茅舍,山道上偶有人行,草庵偶见门童持帚……停下奔跑,稍事喘息,再爬上一个又一个山岗,奔下一道又一道山坡。一路上,远山朦胧,远水无痕,山带着水,水追逐山,只有遇到清寂单薄的木栈时,山水才渐渐舒展了江河湖岔的雍容,渊渚烟汀上的苇草华滋。画家的欢快成为山脉的一种节奏,在一个速度的伸展中,在一个时间的形式里,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生命接力赛,直到抵达他的桃花源。正如西贤所云,只有当形象反抗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北苑山水图》,理性与浪漫齐驱,有一种趋险而又复归于平衡的自在之力,天纵之才只要率性,那艺术的语言就会以自己的风格而活灵活现。但山水画之于个体的解读困境,董源也难例外。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尺度,指向个体人性的解放,承担批判现实的使命。而中国传统山水画,虽然与之同在一个人文关怀的频道上,皆在理想的、唯美的维度里,传递艺术救赎的力量,但“焦点”与“散点”的指向却不尽相同。中国山水画的笔墨趣味,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一把手术刀去解剖人性,但它可以作为一把锄头,在桃花源里耕读。董源绝不会让他笔下奔跑的欢乐之光,散落在人性的不毛之地或人性的幽暗处,而是引导人性向往他建构的桃花源,而他留给山水画中的救赎精神,也许是出于自我救赎的同时,顺便释放出来的一丝灵魂的光亮。
中国山水画,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开启了自由的审美一隙,历千年以弥补精神给养的不足。从这一点来看,所谓“文化的内在调节机制”无他,唯美而已矣。不能因为集权统治的强势,而无视人性在传统固习里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在美的夹层中寻找自由释放的渠道,尤其是在山水画里开拓的文化的江山,才是自由精神的去处,才是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真正的拯救力量。西方人有天堂可去,中国人有江山可往;西方人画了多少天堂,中国人就画了多少山水。由于文明的差异所滋生的救赎之道,无论有多么不同,生于山水画故乡的我们,都会由衷地奉上敬重与感激之情,感谢山水画的筚路褴褛者,使我们只要在一间世俗的书房或厅堂里,流连在一幅山水画间,便可以获得一次审美的拯救体验。
真山真水的天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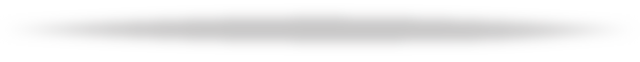
从真山真水的写实到“远观皆妙”的写意,在董源是天真使然。关仝是荆浩学生,在绘画界地位与其师并立,或曰超越其师。但大师也有败笔,米芾至少见过关仝真迹30幅,评曰:“人物俗”。关仝也自知画人物短板,常常请人代笔。
人在山水画中微而妙,须用“点睛”之笔,在时间叙事中呈现空间的真实比例,个中姿态,表达了一种天人关系的襟怀。人与自然的默契,便是人要谦卑地生活在自然的胸怀里,明确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价值分寸,于天人之际确立一种“人文”精神,是中国山水画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
“关家山水”出关中,多在险峻上下功夫,关仝专攻山河之险,每在“峭拔”、“竦擢”处下手,其“刻意力学”,追求“险境”,往往忽略“峰峦秀气”,更拙于安排“点睛”人物之笔,故米芾谓之“粗山”。
荆浩之山,乃个体人格的自我江山,其山势升腾,有如灵魂升华,放浪于苍茫云海,追逐自由而放眼于诗与远方。而关仝山势,好做“竦擢”、“峭拔”状,峰险惊人,执着于山体危耸,用笔如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关山行旅图》,立轴上方,不是高远隐约的轻灵,而是危锋欲倾,直逼眼前,这一笔“倾”成的峰顶,悬于天空,填满立轴的上方,威压视觉;而他在山脚下密植如张弩驳杂的枯枝纷纷刺向天空,忙碌的人群则如蝼蚁般匍匐于土地上,如此的视觉冲突是震撼的。在构图上,“头重”而“脚轻”,并非愉悦的审美体验,表明关仝的山水抱负或是个体境遇的况喻,所呈现的精神样式,不再是关乎自我江山的自由抒发,而是表达现实在大山危耸语境中的江山威迫感,在现实与山水理想之间的个体自由意志,似乎正面临抉择与晦涩的游离状态。也许这些痛点,才是关仝艺术的审美颜值点。他可以屈服于自然,但他痛苦的张力不会在回归自然中与之和解,他不会给树枝一片绿叶,更不会给出“小人物”的舒适姿态。
比起关仝的用力,董源显得轻灵,如果说关仝仅得荆浩之一体,那么董源便得其山水本源与初衷;如果说荆浩以北方山水构建理想国的样式,那么董源则在江南描绘桃花源的愿景,而《潇湘图》则表达了“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江南山水景象。
董源还有一幅《洞山天堂图》,可知他对桃花源天堂般的憧憬。但无论他有怎样的憧憬,董源每一笔却都落在江南的真山真水上,山头苔点皴密,水天云晦氤氲,峰峦若潜龙隐约,汀渚溪桥连接垂钓人家,一如沈括所言“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而是真山真水的天真烂漫。董源无需炫技,亦不做惊人之语,但皇家富贵气、文人书卷气、院体大匠气都集合在他的麾下,活泼起来,汇流之后,形成率性的自由格调。后世临摹董源,也许会有一种消解虚高自我的天真愉悦感。
都说文人画溯宗王维,王维用“破墨”作画,浓墨未干便施淡墨,淡墨未收又抹浓墨,一层层,浓淡氤氲,很容易乱了分寸。董源以天真作为“破墨”的底气,在江南山水上皴出一派淡雅的视野。凭借这视野,他对皇家金碧山水进行水墨调制,在淡设色中,山水泛泛淡淡的,都是江南烟雨的写实。
沈括一边称董源写实,一边又说他的画“大体皆宜远观,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返照之色,此妙处也”。近视不类物象而远观皆妙,妙在艺术追求对于具象的突破,开了写意先河。
荆浩以其个性开宗立派,董源则具有大宗师的格范。他把荆浩那种尖锐的精神穿透力涵养成天真的圆融,将设色与水墨、写实与写意统一起来,在他从院体过来时,随着他将皇家山水降解到水墨,又让设色走进水墨中,归于绚烂后的平淡。同时代追随他的学生有巨然和尚,宋代有米芾、沈括等人,元代,取法董源的风气渐开。汤垕认为:“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如(董)元又在诸公之上”。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直至吴门画派才真正完成了中国文人画流派,而吴门画派宗师董源,董源实为中国文人画之源。
(作者近著《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信出版社)

 经 济 观 察 报 ∣理性 建设性
经 济 观 察 报 ∣理性 建设性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