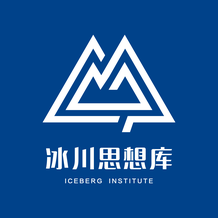到城市工作的农业劳工一旦工作结束,由于负担不起城市的生活水平,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落脚地,只得返回乡村。但是即便回到乡村,他们也无法再找到工作。
本文是对荷兰经济人类学雷曼教授做的一次专访,请他就其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印度劳工的生存状况,谈了他的研究和感受。
王珊珊:布雷曼教授,您好! 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据我所知,您长期从事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农业劳工生存状况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我想首先请您谈谈您对印度的实地考察和相关研究的情况。
布雷曼教授:1961年,我刚到印度,那时候的印度被称为“印度村”,85%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大多数人又居住在人口500至1500人的村子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持续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西爪哇的土地和劳动力状况,在印度做田野调查,并把我的发现置于历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

▲印度农村
到印度后,我在巴罗达市住了一个月,看了居民和人口普查的报告,还有大学图书馆中所有关于印度殖民地的材料。在那里,我发现了契约劳工的问题。
我最先研究的两个村子是位于古吉拉特的南部、 孟买北边几百公里处的其克里格玛 (Chikhligam)和甘德韦格玛 (Gandevigam)。
在古吉拉特乡村,村子根据种姓对人进行明确的划分: 婆罗门地主住在村子的中心,通常是两层楼的砖房。哈尔帕提(Halpati)种姓的农村劳动力部落,人口更多,住在郊区由自己建的泥屋里,没有自来水和卫生设施。他们的上一代曾经是契约劳工,听命于地主进行耕作。他们仅有很少的安全保障和收人回报:工作时候的一顿饭、饥荒时候的粮食配给和帮他们渡过如疾病等家庭危机的贷款。
印度独立后,契约劳工制被废除,虽然官方称再也没有契约劳工哈里斯(halis),只有自由的、白天工作的劳动者,但他们的某些境遇令人感觉他们比上一辈人的遭遇更惨。
印度国会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赞同的观点认为,印度成为殖民地以前,农村的村子是一个和谐、自律的社区,在那里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相互合作,关系融洽。殖民地的统治毁掉了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促成了一个无地劳工阶层的出现。
通过强加现金土地税,又破坏了村子赖以维生的经济。随着经济货币化和农业发展的停滞,农民被迫出售他们的土地,无地的人数增多。当然,由于英国的统治导致债务逐渐增多和土地渐渐被分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印度农村
土地所有权构成契约仆人哈里斯对地主长期的、继承性的依附关系的基础。奴役因为缺乏雇佣选择而被固定,弱者只能从地主那里寻求安全和保护。
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奴役哈里斯,而且因为广泛的内部种姓关系,这种奴役变得固化。高级种姓的地位保证他们接受货物和服务,而低级种姓负责提供这些。圣雄甘地曾希望通过村务委员会体制,回到原来质朴、和谐、民主的村庄。
民族主义者常常把村庄描绘为一种反对殖民地统治的堡垒,在这里,人们彼此依靠,生活得十分幸福。但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村庄里原有的不平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构成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被否定,英国使村庄社区制度化,并形成一个形式简易的政府,社区权力的划分则有赖于殖民地的统治者。
由于资本主义和货币化,哈里斯制度逐渐衰退了。个人担保被打破,尽管债务奴役依旧十分普遍,甚至许多低级种姓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5月要带上全家人去孟买外面的砖窑工作。

▲孟买是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
王珊珊:您认为1950年1月独立后,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吗?
布雷曼教授:我认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印度的独立实际上强化并固化了地主的权力。在印度的乡村,政治民主永远无法变得可操作。权力还像以前一样,村务委员会还是由高级种姓独占,时至今日也没有改变。
例如,在甘德韦格玛村,名义上的村长是一个占村里人口多数的哈尔帕提妇女,但她是个文盲。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村子和八斗里格玛村,村长都只是各村高级种姓的副村长的傀儡而已。 甚至出现过哈尔帕提因向八斗里格玛村的高级种姓抱怨而遭到残酷对待,被鞭打致死的事件。
独立前,部落一直由高级种姓统治。圣雄甘地从古吉拉特开始发起一场社会运动, 希望通过国会甘地主义者的努力使部落的人民公民,使下等种姓成为公民。后来在一定程度上,部落人民成了公民。这对国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选票库。但这些被称为“激进工人”的甘地主义者表现得并不像是工会,他们从来不要求高工资和良好的雇佣条件,认为独立后自然就有了。

▲印度印度后,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然而,尽管独立后,每个人都有权利投票,但是投票箱基本上由本地的高级种姓把持,他们监管投票,以便使票都投给他们支持的候选人。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地主站在他的稻田上,他说:“我可以在这种夏稻,但不种,因为那样就要雇佣劳工,我不想这么做。”这句话中除了表现出不平等外,还让人明显地感受到阶级仇恨的存在。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高级种姓的人,他反对《国家乡村雇佣保护法案》,他说:“这些人没什么用,他们的基因是劣等的,有缺陷。”他接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代又一代,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很虚弱的,是弱等种族。” 这种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在其他地方也常常可以听到。虽然也会有人起来反抗村里的统治,但往往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的变化非常少。由福特基金会强力推动的绿色革命带来了更多的肥料和杀虫剂,还有更加现代化的设备,但主要获益的依然是地主阶级。
事实上,绿色革命并没有改变印度农村潜在的劳动关系。例如,当甘蔗收获时,大地主还是喜欢用有工头的马哈拉斯特拉的劳动者。虽然当地有许多劳动者,但是一旦个人依附解除,他们讨厌与哈尔帕提有任何关联。
在1963年至1971年间,农业劳工的工资实际上下降了,部分原因是由于使用外来劳动力所致,而农业劳动力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和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了。控制人口运动导致了局势紧张,因为运动盯着低级种姓,提出做绝育的给80卢比,导致社会的不公平。

此外,地主的孩子不再对农业有兴趣,想走出村子从头开始。因为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钱和许多的社会资本,与村子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许多人去了英国或美国,做非定居印度人,他们在新国家是莫迪的追随者。他们不再关注农业,在其他地方投资,但土地依旧在统治种姓的手里。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确实有一些温和的改进。有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主要由于在古吉拉特进行的劳动力密集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人有了自行车,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找工作。但是90年代, 随着辛格重返新自由主义,大多数改进都消失。
王珊珊:新自由主义出现后,印度的农业劳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布雷曼教授:首先,最大的特点是农业劳工的双向循环流动,而不是单向地离开农村去城市。
在村子里,一个工头可能招募一大批劳动者去收割或者去几百公里远的另一个邦的砖窑工作,或者招募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工作。但到城市工作的农业劳工一旦工作结束,由于负担不起城市的生活水平,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落脚地,只得返回乡村。但是即便回到乡村,他们也无法再找到工作。
这种劳动力机制使乡村和城市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农业劳工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在减小,在城市也没有定居的地方,面临两难困境。

其次,非正规经济可能变得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它造成的问题跟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一开始它通常被定义为城市现象,最早有重大影响的文章是基思·哈特1971 年对加纳的研究。
他记录下在阿克拉街上可以看到的各种谋生的生意:卖食物和酒的摊贩、搬运工、擦鞋工、 苦力工、捡破烂的、小偷 、皮条客等等。国际劳工组织委托达喀尔、阿比让、加尔各答、雅加达、 圣保罗的人类学家进行的研究发现,非正规经济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城市的特征。 但是事实上乡村经济也有许多“非正规”的特征,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经济以自我雇佣为特点,如此多的“小企业家” 只是需要增加投入,变成充分发展的小资本家,但是这种自负盈亏的工作通常只是劳动力工资的伪装形式。街头摊贩在早上以现金购买货物或从批发商和中间人那里得到委托,然后晚上把没卖出去的货物返回,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在家工作的工人从中间人那里得到原材料,然后中间人收回制成品,付给一点工钱。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正规部门是一个无限扩大的就业 “安全网”,可以吸纳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但如果一个城市充满了建筑工人、街头手工业者和摊贩、捡破烂的、乞丐、搬运工,新来的人想在街上站住脚就很困难。
此外,还有很多恶房东和一帮在非正规商业地界巡逻的人。尽管人口一直在膨胀,印度全部经济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业大概从2004年就已经停滞,我发现在2011年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人口的流转已经减慢。
我们需要了解经济的全部结构,包括所有组成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部门。正规的特点是范围大,资本密集运行,有更先进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结构、复杂的劳动等级、管理规则和税收等。

非正规的特点是低资本密集,低生产力、回报快、技能要求少、利用家庭劳动和资金、客户少,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廉价,这两个部门相互渗透。在乡村经济中有正规的经济——造纸厂、糖厂和一些工农混合类型的工厂,而非正规劳动力则加工、收割牧草、甘蔗,或者参与建筑和修路。
在正规的经济中,大量的农业劳工在非正规的情况下通过外包或转包被雇佣。非正规经济是削减劳动力价格的简单手段,把它削减为纯粹的商品而不要求安全和持续的工作条件,更不用说寻求保护、预防意外了。
你购买劳动力因为你需要它,用完就结束,这就是非正规经济的一般方式。另一方面,为什么非正规经济在雇主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如此受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不会提到的)?
因为这使集体行动变得非常困难,劳动力变得非常分散,很难组织起来。如果工人白天站在早市出售劳动力,怎么能加入到周围人或竞争对手的集体活动中去呢?这是农业劳工今后谋求自身权益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本文摘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2期,原标题为《亚洲农业劳工生存状况研究:以印度等为例》。为便于手机阅读,我们进行了删节,重新分段,个别字句做了调整,并重新制作标题,配了图片。如有引用,请核对原文。因无法联系作者,欢迎版权单位和作者与我们联系稿酬事宜。
.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