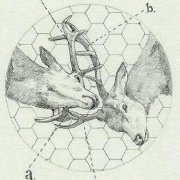作者:小芳 啵儿 陆缘 春妮
北京买房故事 出品





图:向右活动查看村中景象
11月25日的搬离最后期限之后,新建村的人少多了。
这个靠近北京南六环的村庄命运,是从一周前的那场公寓大火开始改变的。很快,“离开”成为村里的主题。
离开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新建村每年都会经历一场大规模别离——春节前,也就是冬天最冷的那段时间,平日里寄身在群租房、公寓里的外乡人,会三五成群地拖着行李离开,返乡过节。再如同候鸟一般,节后从各地涌来,重新融入在新建村棋盘一样又小又破的街巷里。
周而复始的,村子里总是这样,一次次在冬天空了,又在春天满了。当然,这次不太一样:旧的新建村正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而那些冒着凛冽寒风离开的人,大多不会再回来。
他们来不及告别。11月26日,村里一片寂寥,到处是凌乱的垃圾和工厂废墟,空气里混杂着异臭、羊毛和尘土的味道,多数人家房门紧锁,主街两侧的商铺牌匾七零八落。偶尔还会有搬家的身影:有人把打包好的行李搬运上车,有人从胡同里抬出最后的家电。
寂寥之下藏着另一种热闹:
收废品的小哥骑着摩托在大街小巷吆喝,生意没前两天多了,但20块还是可以收到一个饮水机;记者、志愿者和做社调的大学生们拿着相机和笔,忙着记录下这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地方——这个默默无闻的城中村第一次吸引了来自打工群体之外的关注;穿着橙色马甲的巡逻员和肩扛铁锹的保洁工串游在马路中间,一边张望一边在废墟里搜罗着可以捡回家的宝贝。
不过,这样的热闹应该也不会持续太久了。属于这个村庄的往日时光,跟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们一样,变成了一盘坠落的水珠,迸裂,四散开来。
搬离
已经是11月26日夜里8点多,王英还不想回家,她哆哆嗦嗦猫在自家车里,“别管怎样,车里还暖和一些,屋里太冷了。”大火之后,王英从新建村的聚兴公寓搬了出来。临时住所里没有电,没有暖气,零下5度的北京冬夜显得很难熬。此时,她的手机也快没电了。
刚到新建村的时候,王英卖过衣服,后来有了孩子,就专心带娃了。
她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最见不得孩子们惊恐的眼神,同时,这个来自河南乡下的女人也小心翼翼地对待外界的接触,在连续诉说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后,她又把微信语音都撤回了。“是不是说得有点多了?”她不安地问道。
搬家对她来说像是一场突然袭击。
大火第二天早上,她就问房东要搬吗?房东答:不知道呢。等她11点多回来,房东却匆忙告诉她,“快点搬,晚上8点之前都要搬走。”
王英赶紧给还在厂里上班的老公打电话。搬家时来了一群维持秩序的人。王英也想赶紧搬,村里那场大火让她心有余悸,不过,搬家也让她很心疼——两年前花2000多买的冰箱,60块钱就卖了。这就是村里此刻的行情,收废品的人游荡在村里,低价收入饮水机、洗衣机、冰箱,还有不少人到处转悠着翻捡垃圾,“有人在丢掉的衣服里捡到1000块钱”成为他们口口相传的新闻。

图 | 家具电器以最低廉的价格被收走
匆忙成为了搬离的主旋律。王英有点不舍自己的冰箱时,旁边收废品的人不太耐烦了,“你快点,人家那新洗衣机都咣当一锤咣当一锤的砸了。”
同样着急的还有房东,他的租户大多都在厂子里干活,情急之下,拿着手机的他竟然不知道该先通知谁。
王英和丈夫最终在一片乱哄哄和孩子的哭声中,把行李拉到了不远处的朋友家,算是暂时落了脚。但这样的安稳只有一夜,第二天,朋友家也得搬,他们又借住到一家厂子里,26日一整天,王英都猫在车里刷手机找房子。
跟王英不同,33岁的潘进最初并没有意识到那场大火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住处离事发公寓只有500米,当晚,要不是手里有活没干完,加上听说现场戒严,他其实是想去看看“当大官的人到底长啥样”——他在朋友圈里听说村里起火起了人,还来了大官。
潘进是有好奇心的,4年前刚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爬长城,“比赣州的古城墙还是要牛”。这几年,服装厂生意还不错,他打算等4岁的女儿再大一点,就接到北京来,”让她见见世面。”
不过,如今这一切都不太确定了。“明天吧,明天我就回老家,等明年再做打算”,潘进擅长安慰自己,把这次回家当成提前放假,“损失重的还是那些工厂,我最多损失两三个月工资而已。”
事实上,这里很多人对“离开”保持一种冷静决绝的态度。在个体命运被时代洪流冲击改变时,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保持沉默——相比发牢骚,生存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穿着红色棉拖鞋,窝在一条临街长凳上看剧的张友爱就显得很淡定。不知道亲戚叫的搬家车什么时候到,她在这里打发时间。家里的网被断了,她好不容易找到有WIFI的地方,忙着缓存几集《将军在上》,但即使是中午1点的太阳下,空气里还是冒着寒意,她左手托着手机,右手夹在大腿中间取暖,每隔十分钟就得倒换一次。
她是做女装的,之前在广州呆过,五年前来北京,至今还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她喜欢住在城中村,“东西便宜,什么都有”。但现在她打算回老家了,“北京留不下的,早晚要走”。





向右滑动查看匆匆搬离的人们
而很多人没有搬太远。
周边十公里左右的村镇成为他们的落脚处。来北京18年的袁红在大兴魏善庄找到了一处院子,租金一年两万。不过,因为是连夜搬家,她现在还不知道新住的村子是什么样,只记得路很窄,“跑两辆车都费劲,条件也比新建村差多了。”
从地图上看,魏善庄处于南六环外,再往南走走,就是廊坊了。村子里没什么卖东西的,房东告诉袁红,买东西需要去镇子里“赶集”。
北京的确给了袁红更好的生活:如今儿子和女儿都在北京工作,她自己也在黄村有份相比之下比较体面的工作:卖保险。“魏善庄那边的房东自己还种白薯呢”,只有说到回老家时,这位爽朗的女人才会面露迷茫,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快40岁了,回家能做什么呢?”
留守
新建村里难得地保留着乡土人情。这里与国贸、中关村、西二旗都不一样,与土著们扎堆的老北京胡同也不一样,结伴而来的老乡、亲戚们在这里形成一张张关系网,事实上,这是大部分外地人最初来新建村的理由。
在老乡家厂子住了几天的王英,如今最能体会这份温情——借住的第六天,他们一起吃了顿丰盛的午餐,三素一荤,王英特别强调了其中“还有肉和馒头。”
在腾退中的新建村,吃饭是个大问题。饭馆和菜市场都没了。
在城里跑出租车的胡先生坚持用车拉回了米面和蔬菜,偷偷开火,屋外用木板搭建的小厨房上,还放着没有刷的碗筷。有人还会把煤气罐藏在洗手间里,但更多人放弃了执念,村头的李大爷已经吃了两天泡面。
如今留守在村里的多是土著,还有些钱没拿到手的打工者。38岁的杨宁昨天还在村里呆着,他还没收到房东退款和工厂工资。

图 | 皮包的主人曾在这里蹲守了3天
他是2007年来北京的,他原本在家种地,奥运会那句“北京欢迎你”让他充满希望,“最重要的是在老家找不到媳妇儿,还有就是想看看大城市的样子”。可惜十年过去,他还是光杆司令。
因为胡子拉碴,杨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他不好意思催老板太紧,“他们也不容易啊,这得损失多少啊”,这位山东汉子站在寒风中替老板发起了愁。
一些小工厂、小作坊的老板们也还在滞留。
图 | 如今空荡荡的厂房
见到朱顺时,他正双手插兜,静静站在店门口,对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发呆——
他是做门窗生意的,有一万多块钱的材料不知如何处理,还有四五万欠款没来得及收回。在北京14年,他在前几年挣到了钱,除了养活一家七口,每年还能剩余万把块钱,这样的收入,比在家种地好多了。
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今年到现在,朱顺只到手了1万多块钱。如今,他只想赶紧收回欠款、卖掉物料回家去——他本来想把物料当废品卖掉的,但等下定决心的时候,村里的废品回收站已经关门了。直接扔掉?他实在舍不得。
而那些欠款也不知何时能讨要回来。“给欠钱的人打电话,人都不接了”,他声音微微颤抖,又长长叹了口气。实在等不到,他也就只能回老家了。
往昔
失去外地人的新建村,被甩入了命运的漩涡。
头发花白的董华在2007年盖起了自家的楼房,在他的印象里,那是村里第一批楼房,在此之前,大家都住着大院子式的平房,庄稼地里种着白玉米,工厂很少,“只有老曹的纸箱厂”。
慢慢地,工厂多了,楼房起来了,外地租客也涌进来了。新建村变成了大兴出租车不太爱来的地方,“人杂、乱、马路特别窄,两辆车错开都费劲”,刚从新建村拉了一家东北人去北京站的刘师傅这样发着牢骚。

图 | 一处标着“回家了”的库房已经被废弃
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租客们,新建村的杂乱意味着世俗温暖。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快递员、送餐工、服装厂员工、建筑工人,他们贡献出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便利,但那些毕竟不属于他们。
只有新建村才是真实的。
王英在新建村生活8年,在这里认识的人比在老家的还多,“这里的人都特别好”,这句话她说了三次。她喜欢这里的生活:
一出门就可以买到蔬菜、水果、干果和零食,大家彼此都认识,关系也不错,即使是嘴馋了,抓把干果吃也没关系。村里有很多吃麻辣烫、撸串的地方,夜里12点才关门,火灾发生前十天,她和朋友还去了村里的KTV唱歌,王女士把视频发到朋友圈并配上文字:“太吵了”。
如今,这些透着烟火气的吵闹终究是消散了。拆迁机器的轰鸣声、搬家的嘈杂声,大人的吵架和孩子的哭声,都一起笼罩着火灾过后的村子。
对于土著们来说,靠出租房屋赚钱的日子要成为历史了。董华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如外地人,“人家可以回老家,我们去哪呢?”

图 | 留守的老人用小车从远处拉回一桶水
村里一些老人们还记得新建村过去的模样。
75岁的张敏英是61年前跟父母从昌平迁来的,一起来的是几个村子的人,村子也因此得名“新建村”。在村里生活一辈子,张敏英熟悉这里的一切,也知道哪里的房子最值钱。
比如主干道上的房子租金要贵些,一家店铺一年就能收入10万,而张敏英家由于在里街,四家商铺一年才收10万。如今,这四家商户已经全部撤离,门前只剩残缺的店牌,但老人仍能从北向南依次指出:烟酒茶行、饭馆、中国移动和足疗店。

图 | 曾经的超市被挖掘机弄弯了招牌
不过,发生在新建三村的腾退,对张敏英似乎影响不大——老人家里四世同堂,最小的重孙已经5岁。外头搬家的声响再大,她每天6点半起、10点睡觉的规律生活依旧雷打不动。只是,昨天她听说了有女人夜里抱着嗷嗷哭的2岁小孩出去找房子,觉得有点心寒,她最见不得孩子受苦。
前路
往日的生活痕迹正在迅猛地从新建村抹去。
“羽绒服60一件,低价甩卖了”,11月26日上午,新建三村村口,温州女人张淑萍正努力在大风中叫卖,她三轮车里的男士羽绒服只剩最后5件了;一家甘肃人从早上就开始收拾,到下午3点都没顾得上吃饭,等车一来他们就要直奔火车站回老家了。
等待丈夫找车回来的张园园一直站在家门口张望。她在村里生活了6年,一直在缝纫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拿上五六千元,但每天需要工作15个小时,没有五险一金。她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北京城长什么样——她的生活半径一直在新建村附近,疲于生计的人大概是没有什么心情欣赏风景的。

图 | 新的招工信息又贴上,不过这次不在北京
南六环的生活,是生活在市区的人们无法想象和理解的。跟张园园一样的人有很多,杨宁来北京10年,上一次进城是在3年前,陪朋友去了25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说到这,高中没毕业的他双眼望了望天,极力地想出了一个形容词,“天安门很大、很大”,他又强调了一遍。
事实上,除了上班,他基本不怎么出门,也很少有娱乐活动。“这儿啥也没有,还不如多睡会儿。”村里最受欢迎的一项娱乐活动是搓麻将,花30块钱就可以在棋牌室消耗一下午。
如今,30块钱的棋牌室,跟10块钱一次的理发店、公共浴室一起变成了过往。离别太突然,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告别。
这让王英有点难过。“以前大家都热闹地在一起,现在这些人都不知道去哪了,那个卖干果的大姐也不用手机,怕是联系不上了。”
在北京这座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里,这样的分离或许就意味着永别了。曾经拥有过相似喜怒哀乐的这群人,随着旧村庄的消失而各奔东西,有人去了更加偏远的农村,有人去了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河北,更多的人暂时回家,等待过年,也等待命运的转机。

图 | 站在废墟里玩手机的小孩
连本钱都没赚回来的朱顺,现在不敢回家,即使回家,这个春节怕也是过不好的——按照往年习惯,他会在年末把外面的欠款都收回来,带着这笔钱回家,让父母、妻子和三个孩子开开心心过个好年。
但如今,拿什么回去敲开家里的那扇门呢?
注: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你还可以在一点、企鹅、头条等平台找到我们。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