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雷蕴含 天津摄影报道
冬日的南开园,湛蓝天空下湖面温柔。马蹄湖的荷塘虽然凋零,但生机犹存,让人想起李商隐的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李商隐是叶嘉莹先生生前投注众多生命热情给予阐释的古典诗人。她曾说,“我遭遇到很多人生中的挫折、苦难、不幸的事情,我都是用李商隐的诗来化解。”只是马蹄湖的这些冬景,再也等不来赏荷吟诗的叶先生了。
2024年11月24日,有“诗词的女儿”之称的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叶嘉莹先生逝世,享年100岁。11月30日,叶嘉莹先生的告别仪式在天津举行,封面新闻记者现场吊唁。
 叶嘉莹先生追思会
叶嘉莹先生追思会叶嘉莹农历荷月出生,小名“小荷”。她写过不少咏荷诗。而巧合的是,南开校园的一个重要景点马蹄湖,一到夏天满塘荷花。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执教几十年,幽幽荷香,浸润过她的生命。她曾写诗表达自己与南开的情谊,“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修到马蹄湖畔住,托身从此永无乖。” 很多人在南开看到荷花的时候,天然会想起叶嘉莹。一个地理空间,与诗意世界,形成了互文对照。
 南开大学马蹄湖
南开大学马蹄湖众人送别
“天池定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里”
叶嘉莹逝世后,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逸夫图书馆内设有追思灵堂。为便于各位友人追悼,南开大学特别开设了专门的入校申请通道,方便校外人士间前来吊唁。在过去几天内,学生、老师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纷纷来到现场吊唁。
灵堂中央,花圈层层簇拥着叶嘉莹先生的遗像。照片中的她面带笑容凝望远方。由叶嘉莹先生弟子、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汪梦川题写的挽联“一老证斯文,从忧患修来,作词中仙、天下士;百年闻至道,守孔颜乐处,是仁者寿、圣之时”,置于遗像两旁。
 设立在南开大学内的叶嘉莹先生追思灵堂
设立在南开大学内的叶嘉莹先生追思灵堂11月30日上午10时,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天津第一殡仪馆滨河厅举行。现场,大屏幕上打着一句诗:“天池定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里”。
冬天的天津,气温较低。封面新闻记者看到,南开多位学子及叶嘉莹亲友陆续赶来,现场还特别设置了“社会人士等候区”。虽然是周末,早上8点多,已有很多人在“社会人士等候区”等候入场。其中有从上海、郑州等外地赶到天津的90后、00后,也有天津本地的退休工人,他们都是深受叶嘉莹影响的诗词爱好者。
来自上海的90后孔女士,此前听过叶嘉莹的讲座,深受感染,这次趁周末,她坐了一夜火车,早上直接拉着皮箱赶到天津,送叶先生最后一程。她还在火车上抄写了一段《古诗十九首》表达哀悼:“叶先生讲过《古诗十九首》,特别精彩。”
照顾叶嘉莹生活起居7年的保姆王女士,神情沉痛,与叶嘉莹回国后带的首位博士生迟宝东讲述着叶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言语呜咽,“叶先生年纪100岁了,是高龄,我们不能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这天真的到来了,还是不太接受。叶先生此前一直状态还不错。走前三天,叫她都是有回应的。她走的时候,没有受罪。”随后,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王女士,她说:“叶先生人特别好,没有一点名人架子。我跟着她7年,她对我特别好。”
为弟子张静新书作序,借陶渊明表明心迹: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比起那些专注在书斋里写专著、论文著作等身的学者,叶嘉莹一生花费很大精力投入在诗词教育上,努力促进诗词润及现代社会。在自己的书《我的诗词道路》的前言中,叶嘉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剖析自己的心路:“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作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叶嘉莹用生命体悟诗词、传播诗词,将诗词感发的力量升华为荡涤心灵的能量,在无数人心间播下文化的种子。在叶嘉莹的诗学理念倡导下,南开大学文学院大力推动“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诗教润乡土”等活动,继续致力于在现代社会中将诗词营养落实到普通大众中。
张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叶嘉莹嫡传弟子。她先是跟着叶嘉莹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就留在叶嘉莹身边工作,与她“携手日同行”已有20多年。
2012年3月至2015年9月,每逢春夏之际,她都会陪同叶嘉莹飞至温哥华,共同工作、生活和学习,见证了叶嘉莹生活简朴、惜时如金、坚强豁达的珍贵瞬间。
张静回忆,2014年7月下旬,叶先生在家中收拾回国装箱的资料书籍时,不慎摔倒,腰部扭伤。“几天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为叶先生举办九十华诞庆祝会,她坚持站着用英文发表了半个多小时的讲话。第二天伤痛加剧,下床都十分艰难。我虽然就住在她卧房隔壁,但叶先生从不喊我协助,每次下床都坚持自己在床上挣扎盘旋良久。”
在2024年10月出版的《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中,张静以恩师的诗词生命为切入点,从弟子角度揭秘叶先生的为师之道、诗教之路,以及她讲诗的成功经验和魅力所在。
 《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
《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在为弟子新书《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所作的序文中,叶嘉莹再次阐述她对师生关系的理解。古典文学专家龙榆生先生曾经给他的学生题写过一首《浣溪沙》的小词,下半阕说:“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叶嘉莹写道:“我曾把这几句改写了一下,变成‘师弟因缘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比骨肉更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来的,是血缘的关系,而不在于个人精神、思想上有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是寄托在诗歌里面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志意,我们还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学生。”
叶先生在序言中,还提到“作为一位百岁老人,我知道自己少不了会被人评说”,她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来表露心迹。对张静写她的书,她说,“除了学生对老师的溢美情辞愧不敢当,内容都是可信的”。序文的末尾,她作诗感慨人生:“天外从知别有天,人生虽短愿无边。枝头秋老蝉遗蜕,水上歌传火内莲。”
郑州高中生专程赶来吊唁
受影响决心“以研究古典诗词为志业”
1979年,在海外已拿到终身教职,生活安稳的叶嘉莹,主动申请回国义务讲学,身体力行将自己的身心投注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教育和传播。受友人之邀,她来到南开大学执教。晚年她个人累积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志在全球弘扬中华诗教。她希望,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
 30日上午参加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队伍
30日上午参加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队伍她的心愿没有落空。如今,古典诗词热正在年轻人当中兴起。
来自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的高二学生张梓烨,是专程来吊唁的其中一位。他所写的两首挽诗也被收入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公众号上。其中一首《挽诗赠叶嘉莹先生》:“旧筵今是葬坟台。黉泮楼前暮雨哀。挽寄许随潘诔去,离魂不解宋招来。薄逢未可歌时运,多难犹应造栋材。为有恩深倾汉帝,奠前频洒孔遗杯。”
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张梓烨谈到,还在读初二的他曾参加了央视《2022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录制,从此开始读叶嘉莹先生的书。因为被叶先生一篇叫《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长篇论文所深深折服,由此产生了将来“以研究古典诗词为志业”的想法。得知叶嘉莹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感到“万分悲痛”,在家长的陪伴下,坐高铁来到南开园,送上他的一份感谢和追念之情。
阐释古典诗词的学者很多,为什么单单被叶嘉莹深深打动呢?张梓烨说,自己还读过其他学者谈中国古典诗词的书,也受益匪浅。但激发自己立志要系统学习、研究古典诗词的,还是只有叶嘉莹先生的作品。“叶嘉莹先生是一个感性和理性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个人。她具有特别细腻敏感的心性,比如对于李商隐的一些公认非常难解的作品,例如《燕台》《海上谣》等,她都能够从中获取到非常细腻深刻的感情信息。我觉得这样的鉴赏能力,不仅需要后天学习、训练,还需要足够的先天禀赋。在理性的一方面,在我看来,叶嘉莹的考据功夫也都是非常深的,比如从她写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可以看出。”
叶嘉莹去世消息传来后,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张元昕就从美国纽约飞回天津。张元昕14岁时,被南开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成为叶先生年纪最小的爱徒,跟着她学习了6年。在追思会上,张元昕说,“诗歌是全息的,它承载着每一位诗人的生命。叶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诗歌的全息,什么叫做诗教,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形式,也是一种情感的教育,一种伦理的教育。我在先生身上看到的是整个生命状态的学问,是以心应心的知行合一的学问。叶先生已经把灯传下来了。作为学生,我们需要用一辈子去努力完成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她还透露,如今她已效仿恩师投身中华诗教事业,和家人一起在海外开班传授中国古典诗词创作和欣赏。
 30日上午参加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队伍
30日上午参加叶嘉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队伍为什么她的诗教影响力格外大?
“把自己整个生命融进去了”
对古典诗词的当代研究者、创作者众,名家辈出,但叶嘉莹在古典诗词教育与大众传播领域内的影响范围,尤为突出、广泛。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提到,在研究和传播古典诗词领域,叶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她把自己整个生命融进去了,既是一个研究者,一个传播者,又是一个践行者。”
1979年春,叶嘉莹回国执教,其诗词教育风格给教育界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很多同学们惊呼:“诗词,可以这样讲!”1979年4月24日,叶嘉莹在南开的第一讲,是在第一阶梯教室。她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同学们全都吸引住了。此后,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堂课,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叶嘉莹还作了诗,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迦陵学舍门口(拍摄于2024年11月29日)
迦陵学舍门口(拍摄于2024年11月29日)叶嘉莹曾为南开大学中文系1977、1978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很多学子至今仍记得她在几十年前上课时的盛况——能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不光加座加到了讲台边上,连门口、窗边都挤满了人。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张卫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是当年亲身感受叶先生讲课魅力的学子之一。张卫说,“她的课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她讲课的方法,关注的重点,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古典文学。她带领我们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让我们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宝库。”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卢桢教授在南开学习、工作20多年,虽然不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但也多次听到叶先生的课。据卢桢教授向封面新闻记者回忆,在叶先生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他多次跟一些诗词学会社团到叶先生的住所讨教先生。他记得有一次,“先生问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不写诗?我说我写过,但写得不太好。先生就鼓励我说,无论是新诗还是古典诗歌,想写的时候都要把它写出来,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写不好而错过自己想要写诗的冲动。这跟她的一个诗学看法相关:读者个人的感动和诗词精神,如果想要达到一种内在的结合,个人的感动就非常重要——不光读诗时重要,在写诗时也是非常重要的。诗歌关涉个体生命的体验。这个教导对我影响比较大。”
 卢桢教授
卢桢教授弟子回忆:
温润的话语有万钧之力
天资聪颖,幼年受到书香之家的熏陶,加上青年时期在辅仁大学受到恩师顾随的点拨,为叶嘉莹在古典诗词的欣赏和创作上打下深厚的根基。浮世坎坷的忧患经历,使得她在作为师者讲诗论词之时,能以生命体验和直悟进行兴发,所以其解释见解独到,感染力强。可以说,叶嘉莹集深厚的国学功底、精湛的西学修养,深刻的生命体验于一体,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诗学范式。
叶嘉莹曾说,声音里有诗词一半的生命,诗的感情是伴随着声调出来的。学习“吟诵”,更能体会诗歌之微妙。为了传承“吟诵”这种中国旧诗传统特色,她曾每天工作至深夜两点,精挑细选出两百余首适合儿童阅读的古诗词,并于2015年推出《给孩子的古诗词》一书,并为每首诗词录制了“吟诵”视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嘉言妙音。
卢桢教授向封面新闻记者提到,叶先生去世这一周以来,有大量的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其中当然也包括从南开毕业的学生。“我发现,不管是年幼的,还是年长的,大家提到叶先生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点:一个银发的老教授精神矍铄,永远是站着讲课,一讲至少一个小时起,一般是两个小时,最多讲过三个小时。声音抑扬顿挫,会给我们吟诵很多诗。比如说叶先生吟诵的李商隐那首《锦瑟》,我们四五代南开学子都听过。彼此之间虽然年龄相差好几十岁,但是因为叶先生,我们拥有了相同的青春回忆,这就是她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连接。”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出版部主任迟宝东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带的首位博士生。在追思会上,他回忆了自己跟叶先生学习的珍贵往事,“叶先生讲课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她常常旁征博引,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爱跑野马’,但这种讲法却让我们对诗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叶先生的学问不是死学问,而是活的,有生命的,能随时随地灵活运用。她常说诗词是可以让人心不死的力量。”
 叶先生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迟宝东
叶先生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迟宝东迟宝东还提到,叶先生性格温润,在她身边常有如沐春风之感。“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根基是很浅薄的,但先生从来没有流露过恼怒厌烦之意,而是手把手教一点一点带我,从不厉言厉色批评我们,但温润的话语却有万钧之力。记得有一次交作业写字,有错别字。她就说了一句:宝东你是我的学生,这样可不行。当时我真是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先生就是这样,用她的品格和言行来激励我们,自觉地去奋发努力。”
迟宝东透露,叶先生生活非常节俭,尤其是在吃穿的问题上,“有时让我们帮着买一根老玉米,或者一包果仁就是一顿饭,就算做饭也常常是做一顿管几顿,过着极简的生活。但她在学生身上却毫不吝啬。每逢节假日她都会把我们叫到她的住处,准备很多好吃的茶点,或者请我们吃饭。先生门生众多,往往一聚就是一大屋子,大家边吃边聊,天马行空,话题最后往往还会回到了诗词上面。那真是快乐的时光。先生走了,我一直无法接受,直到有一天看到叶先生作的一首词,才有所释怀,有诗词相伴,云水相依,我相信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


财经自媒体联盟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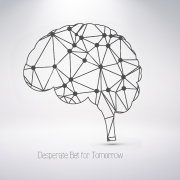






















 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贝壳财经视频
贝壳财经视频  尺度商业
尺度商业  财联社APP
财联社APP  量子位
量子位  财经网
财经网  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