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目前公共卫生安全受到耐药病原体严峻威胁的状况下,具有独特抗菌活性和多元作用机制的抗菌肽被认为是传统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
[1,2]
。新型抗菌肽的发现和结构设计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随着纳米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各种纳米金属在抗感染方面的应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显示出无抗生素策略的潜力
[5,6]
。关键是,一些纳米金属——包括银
[7]
、金[8]
和铜[9]
——已被证实具有类似于抗菌肽的涉及非特异性靶点的多方面杀菌机制。然而,由抗菌肽和纳米金属重组而成的新型抗菌剂一直是缺乏的。氨基端铜-镍结合基序(ATCUN)因为在免疫调节中的重要性而被关注,其是由位于N端的H2N-XXH序列组成;基序中的XX元素可以是除脯氨酸(Pro)以外的任何氨基酸
[12]
。Cu基团可以形成扭曲的方形平面几何形状,通过两个去质子化N -酰胺原子的主链和组氨酸(His)咪唑环快速结合到基序上[13]
。随后,新形成的复合物通过利用涉及Cu1+
/Cu2+
氧化还原对和过氧化氢(H2O2)形成活性氧(ROS)的类芬顿机制,来破坏周边的任何分子银[11,14]
。值得注意的是,Cu位点与H2O2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决定该反应中ROS形成效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银[15]
。受这种天然宿主防御机制的启发,福州大学汪少芸教授团队在这个概念验证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单原子Cu催化剂的氨基端铜-镍结合基序抗菌肽复合物(Cu@G-AMPs)。Cu@G-AMPs功能上可以定位于细胞膜或干扰内部靶标(例如,DNA、RNA和蛋白质),在接近病原体时原位产生并散发出致命的ROS(图1)。最后,Cu@G-AMPs沿袭了抗菌肽的免疫调节特性,会在耐药菌感染的伤口区域发挥出促闭合、稳定肉芽组织、促进胶原纤维增殖、减轻炎症和促进新生血管的功能(图1)。Cu@G-AMPs的出现为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解决耐药细菌已经发展出精确的调控机制来适应抗生素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Fig. 1. Schematicillustration of Cu@G-AMPs’s functional mechanism for healing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wound infection.
结果与讨论
01
设计、制备和表征
新型抗菌剂的主要制备工艺如图2a所示。简而言之,首先通过鸟嘌呤和金属盐混合物的配位热解反应获得了单Cu原子掺杂杂原子的碳基纳米材料(Cu@G);随后,通过酰胺反应将含氨基端铜-镍结合基序的抗菌肽修饰到碳基架构上,创造了不含抗生素的纳米反应器(Cu@G-AMPs),其具有非特异性靶标的抑菌活性。Piscidins-3具有对血细胞溶血率低、与细胞内DNA结合强、能严重破坏细菌生物膜等优点,被认为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候选抗菌剂
[
31
]
。此外,单原子催化剂具有活性位点识别准确、活性可调、金属利用率高等优点[
32
]
;因此,铜的加入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复制甚至放大抗菌肽的氧化还原特性。也就是说,Cu单原子在类芬顿反应中架起了均相催化和非均相催化之间的桥梁,从亚纳米尺度到微尺度都不同于传统催化剂[
33
]
。实际上,单原子金属作为“催化剂”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在生命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氮酶中的钼,血红素中的铁,叶绿素中的镁[
11
]
。实现单原子Cu分散是制备Cu@G-AMPs的关键技术障碍。这涉及到热力学结构基序或非/亚稳相的产生,这需要选择合适的衬底材料来结合金属前驱体,以防止金属原子聚集、团聚和纳米晶体/团簇生长
[
34
]
。因此,直接应用具有高表面积的碳基材料作为衬底来结合金属前驱体,成为可扩展制备Cu单原子的理想解决方案[
35
]
。鸟嘌呤是一种具有共轭双键的嘧啶-咪唑环体系组成的核酸碱基组分,因此本研究指定鸟嘌呤作为合成碳骨架的原料[
16
]
。鸟嘌呤掺杂丰富杂原子形成的底物有利于单个Cu原子的稳定分散[
16
]
。当然,鸟嘌呤固有的生物安全特性是这里采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Fig. 2. Synthetic proces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Cu@G-AMPs. (a) Synthesis process of Cu@G-AMPs, inspired by natural host defensemechanisms involving ATCUN-motif AMPs. (b)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of Cu@G-AMPs. (c) TEM image of Cu@G-AMPs. (d) High-angle annular dark-fieldscan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HAADF-STEM) images of Cu@G-AMPs. (e)Elemental mapping patterns of Cu@G-AMPs (scale bar: 200 nm). (f)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spectra of Cu@G and Cu@G-AMPs.(g) Zeta potential of Cu@G and Cu@G-AMPs. Test concentrations of AMPs, Cu@G,and Cu@G-AMPs are 128 μg/mL.
正如预期的那样,Cu@G-AMPs呈现出类似于石墨烯类材料
[35]
的高表面积片状形态,这有助于单个Cu原子的充分分散(图2b~c)[
35
]
。此外,Cu@G和Cu@G-AMPs的相似外观表明,抗菌肽的改性过程并未改变碳衬底材料的形貌(图2)。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表面结构增强了Cu@G-AMPs和Cu@G有效捕获病原体的能力[
22
]
。为了在原子水平上直接观察Cu的结构,我们应用暗场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HAADF-STEM)对Cu@G-AMPs进行详细的研究。在HAADF-STEM中,由于Cu的质量比C、N和O的质量更大,因此Cu@G-AMPs中的Cu有望在掺杂杂原子的碳衬底上被观察到作为独立的亮点[
36
]
。在2-nm视场中,可以观察到高度分散的单个Cu原子具有更亮的白斑特征(图2d)。重要的是,在更大的视场中观察到的Cu元素除了在单原子状态下随机分散外,并没有以团簇或粒子的形式出现。Cu元素分别均匀地分布在Cu@G-AMPs和Cu@G表面(图2e,附件A中的图S3)。紫外和可见分光光度法的结果表明,Cu@G-AMPs和Cu@G的水溶液在200~600 nm波长范围内没有特征吸收峰,呈非均相状态(见附件A图S4)。其中,鸟嘌呤形成的底物捕获光谱能力差的原因可能是量子尺寸效应强
[
32,34
]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结果显示,涉及N掺杂碳基材料的N—H、C=N和C—N键的吸收峰分别出现在Cu@G和Cu@G-AMPs的500~1210 cm-
1
和1580 cm-
1
波长范围内(图2f)[
37,38
]
。与
Cu@G
相比,
Cu@G-AMPs
的
FTIR
光谱在
1110
~
1210 cm
-
1
和
1400
~
1700 cm
-
1
范围内与抗菌肽修饰相关的吸收峰增强。
Zeta电位测试结果证实含有抗菌肽的Cu@G-AMPs具有比Cu@G更高的正电荷(图2g)。具有适当正电荷的抗菌剂在攻击致病菌或哺乳动物细胞时将有较好的选择性。Cu@G-AMPs和Cu@G的X射线衍射(XRD)谱图在25°附近呈现宽峰,这可能是由于纳米材料中的无定形碳(002)(附见A中的图S5)所致[
40
]
。此外,与Cu@G相比,Cu@G-AMPs的XRD谱图略有向低强度偏移;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抗菌肽的修饰导致原始薄片纳米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此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学发射光谱仪结果显示,Cu@G-AMPs中Cu的含量为0.41%,符合单原子金属催化剂含量低、活性位点丰富的特点(附见A图S6)[
41
]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多种分子结构鉴定技术初步确认Cu@G-AMPs是一种含氨基端铜-镍结合基序和Cu基团的无抗生素纳米材料。根据催化化学的基本理论,Cu@G-AMPs的催化抑菌活性可归因于Cu原子的d轨道与配位非金属原子(如C、N或O)的p轨道之间的强电子相互作用
[
42
]
。作为另一种原因,Cu@G-AMPs的抗菌活性可以被视为与单个Cu原子的离散量子态及其局部化学配位环境密切相关,其中包括最近邻原子的类型和配位数[
35
]
。因此,通过测定Cu@G-AMPs的光热性能和增强的纳米酶配位结构,进一步表征了单原子金属分散状态和底物单原子Cu催化剂。在Cu@G-AMPs和Cu@G的拉曼光谱中(附件A中的图S7),检测到代表无定形碳的峰D(1360 cm-
1
)和峰G(1580 cm-
1
)为[
43
]
。Cu@G-AMPs和Cu@G样品对应的ID/IG值非常相似。通过X射线光电子能谱在Cu@G-AMPs和Cu@G上都鉴定出了代表吡啶N、吡啶N和石墨N的突出峰。Cu@G-AMPs的N谱计算出47.63%吡啶N(397.5 eV)和44.12%吡啶N(401.3 eV)的相对含量(附件A图S8),而Cu@G的N谱显示吡啶N(399.3 eV)的相对含量高达89.83%(见附件A图S9)。有趣的是,吡啶N和吡啶N中的N原子属于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供体,这可以为底物上锚定的单个Cu原子的稳定性提供极其重要的位置[
41
]
。以CuO和Cu箔为对照,通过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XAFS)光谱测定Cu@G-AMPs中单个Cu原子的结构,进一步表征了石墨烯基金属单原子催化剂稳定性和催化性能的基础。XAFS包括扩展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EXAFS)和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XANES)光谱
[
33
]
。具体而言,铜的XANES结果表明,Cu@G-AMPs的能量吸收阈值介于铜箔和CuO之间(图3a~b)。这说明Cu@G-AMPs中单个Cu单体的电荷范围在0~+2之间。相应地,Cu@G-AMPs中的Cu在1.5 Å处有一个涉及Cu—N/O的显著峰,而在2.2 Å处没有涉及Cu–Cu的显著峰,证实了单个金属原子是高度分散的(图3c)。此外,通过对Cu@G-AMPs的EXAFS参数进行小波变换(WT)分析,我们确定了单个Cu原子与相邻原子在K和空间中的真实配位环境。RCu@G-AMPs的轮廓极值(R= 1.4 Å,k=6.7 Å−1
)(图3d)与CuO的轮廓极值(R=1.5 Å,k=6.8 Å−1
)(附件A图S10)接近,但与Cu箔的轮廓极值((R=2.3 Å,k=7.6 Å−1
)(附件A图S11)差距较大,说明Cu@G-AMPs不存在Cu—Cu相互作用,但存在Cu—N/O配位。这一结果与Cu@G-AMPs(图S5)的XRD一致,缺少涉及Cu—Cu晶体的特征峰。这2种表征方法表明Cu@G-AMPs中的Cu在原子水平上是分散的,不会聚合成类似金属晶体的结构。通过对Cu@G-AMPs上的EXAFS的定量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第一壳层中单个Cu原子的配位数约为2,平均键长为1.91 Å(图3e~f),其中图3f描述了Cu@G-AMPs中单个Cu原子与掺杂N/O的底物的相互作用细节)。坦率地说,N和O的固有化学性质对准确识别单个Cu原子在相同键长范围内的杂原子配位环境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34
]
。总之,我们成功地制备并表征了一种具有潜在Fenton类催化活性的新型纳米反应器(Cu@G-AMPs),该反应器是由含有ATCUN基序的抗菌肽和单一Cu原子融合在掺杂了杂原子的碳基衬底上形成的。
Fig. 3. Atom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Cu@G-AMPs via XAFS.(a) CuK-edge XANES spectra of Cu@G-AMPs and referencesamples.Kwas the corresponding energy levelabsorption edge of the element. (b) Amplified CuK-edge XANES spectra of Cu@G-AMPs and referencesamples. (c) Fourier-transformed (FT) magnitudes of the CuK-edge EXAFS signals for Cu@G-AMPs, along withreference samples (FT are not corrected for phase shift). (d) WT of the CuK-edge EXAFS signals for Cu@G-AMPs. (e) FT-EXAFSfitting of Cu@G-AMPs inKspace. (f) FT-EXAFS fitting of Cu@G-AMPs inRspace; (inset) schematic model of Cu–N/Ocoordination.
02
抗菌特性及机理
以MRSA(ATCC 43300)为主要实验菌株,验证上述制备的Cu@G-AMPs体外抗菌活性是否达到预定目标。具体来说,涂布板法的结果显示Cu@G-AMPs对MRSA的抗菌活性取决于处理环境的pH值(图4a)
[
26
]
。Cu@G-AMPs的抑菌作用一般在酸性条件下更充分发挥。SYTO9/PI染色结果也证实Cu@G-AMPs在pH值6.7时对MRSA具有理想的体外抗菌活性(图4b);与PBS和H2O2处理的细菌群落相比,Cu@G-AMPs处理的细菌群落表现出强烈的红色荧光和轻微的绿色荧光。在这里,SYTO9是一种可以穿透细胞膜的染料,任何活的细菌都可以发出绿色荧光,而PI是一种不能穿透细胞膜的染料,只允许膜受损的细菌发出红色荧光[
44
]
。总之,Cu@G-AMPs在酸性条件下表现出对MRSA的抑菌活性,这与传统观点一致,即催化金属通过Fenton-like机制发挥抑菌活性。Fenton/Fenton-like反应的活性和效率取决于H
+
和H2O2的浓度,它们通常在弱酸性范围内具有高能量。此外,Cu@G-AMPs催化反应体系中H2O2的浓度远低于目前临床实践指南(166mmol/L),这实际上避免了高浓度H2O2伤害正常组织[
33
]
。通过MTT比色法测定Cu@G-AMPs对MC3T3-E1细胞的毒性(见附件A中的图S12)。在0~128 μg/mL浓度范围内,Cu@G-AMPs处理的细胞存活率高于75.83%±5.67%。MTT比色结果显示Cu@G-AMPs在抑菌作用浓度范围内具有低水平的细胞毒性。值得注意的是,Cu@G-AMPs在0~128 μg/mL的浓度范围内没有引起红细胞的溶解和破裂(附件A中的图S13)。因此,Cu@G-AMPs具有理想的生物相容性。
Fig. 4.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Cu@G-AMPs. (a) The agarplate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hibition of bacterial growth byCu@G-AMPs at different pH (n= 3). (b) Viability fluorescentstaining of MRSA treated with Cu@G-AMPs + H2O2, H2O2, and PBS was observed using a confocal laserscanning microscope (n= 3, pH 6.7).
Cu@G-AMPs作为一种新型抗菌剂,整合了含有ATCUN基序和单Cu原子的抗菌肽,可能具有一种或多种抑菌机制。因此,我们以TMB为底物检测Cu@G-AMPs固有的酶样活性。理论上,Cu@G-AMPs具有类酶活性,可以将H2O2转化为羟基自由基(·OH),将无色的TMB氧化为蓝色的oxTMB(图5a)
[
45
]
。在这里,我们研究了Cu@G-AMPs浓度与其类酶活性之间的相关性,发现整个反应体系在652 nm处的吸收值呈浓度依赖性增加(图5b)。这一发现表明,随着Cu@G-AMPs浓度的增加,反应体系中的氧化物质(即oxTMB)也随之增加。此外,Cu@G-AMPs的类酶活性随着反应体系pH的降低而升高,这与人工纳米材料的类芬顿反应机理一致(图5c)。随后,2′,7′-二氯二氢荧光素二乙酸酯荧光测定结果证实,任何浓度Cu@G-AMPs处理的MRSA细胞比32 μg/mL AMPs处理的细菌细胞具有更丰富的ROS(图5d)。关键是,随着Cu@G-AMPs浓度的增加,处理过的MRSA细胞中ROS的数量也增加了。这里的“ROS”是指好氧细胞在代谢过程中形成的副产物,包括单线态氧、臭氧、超氧阴离子、H2O2和·OH。其中·OH被认为在所有ROS中对细菌细胞的毒性和刺激性最高[
46
]
。基于这些结果,Cu@G-AMPs具有固有的类酶活性,可以催化H2O2产生以·OH为代表的ROS。
Fig. 5.Enzyme-likeactivity of Cu@G-AMPs.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TMB simulationreaction. Ox was oxidized. (b) Enzyme-like activity of Cu@G-AMPs at differentconcentrations (n= 6, pH 6.7). (c) Enzyme-like activity ofCu@G-AMPs at different pH (n= 6, test concentration ofCu@G-AMPs: 128 μg/mL). (d) ROS formedin situbyCu@G-AMP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n= 6, concentration ofAMPs: 32 μg/m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analyzed using Duncan’smultiple range tests. (**P
存在ROS的外部环境中,MRSA将采用各种保护机制来对抗ROS的刺激,包括产生适应性突变,激活抗应激基因的调控,以及转变为休眠状态
[
26
]
。由于蛋白质是MRSA调控功能的最终执行者,因此蛋白质的情况可以很好地反映生物体本身的瞬时生物学状态[
26
]
。为此,这里采用无标签定量蛋白质组学(简称为“无标签”)技术,从细菌应激反应的角度进一步探索Cu@G-AMPs的潜在抑菌机制。具体而言,与PBS处理的细菌(AMPs/PBS,倍数变化≥2或≤0.5,P调整值≤0.05)相比,从piscidins-3处理的样品中鉴定出106个上调和183个下调的差异表达蛋白(DEPs)(图6a);与PBS处理的细菌(Cu@G-AMPs/PBS)相比,从Cu@G-AMPs处理样品中鉴定出6个上调的DEPs和15个下调的DEPs(图6b);与AMPs处理过的细菌(Cu@G-AMPs/AMPs)相比,Cu@G-AMPs处理的样品中鉴定出223个上调的DEPs和118个下调的DEPs(图6c)。简而言之,AMPs改变了MRSA中大量蛋白质的表达水平,而Cu@G-AMPs仅影响较少数的关键蛋白质。此外,对Cu@G-AMPs敏感的重要DEPs是主要参与了MRSA的传感、调控、修复和重组系统(图6d)。
Fig. 6. Mechanisms of Cu@G-AMPs against MRSA. (a) DEPs inthe AMPs/PBS group. (b) DEPs in the Cu@G-AMPs/PBS group. (c) DEPs in theCu@G-AMPs/AMPs group. (d) DEPs related to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Cu@G-AMPs. (e) GO enrichment of DEPs (n= 3). (f) Heatmap validation of DEPs (n= 3). Different color intensitiesrepresent different numerical values. CC: cellular component; MF: molecularfunctions; BP: biological processes.
为更好地了解Cu@G-AMPs对MRSA抑制活性的机制,将这些DEPs进行GO类别的划分。MRSA中这些DEPs
的统计结果显示,它们主要参与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水平基因转移、
DNA
介导的转化、转化能力的建立以及细胞通讯的负调控等生物过程(图
6e
)。然而,
MRSA
内分配给
CC
和
MF
的
DEPs
很少见;也就是说,细菌细胞通过表达多种参与大范围
BP
的基因产物来响应
ROS
刺激。同时,
MRSA
能够通过调节其抗氧化系统等蛋白表达水平来阻止
ROS
的进一步入侵
[
26
]
。当外界氧化压力超过细菌细胞所能承受的极限压力时,无疑会对细胞的抗氧化系统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
47
]
。因此,与PBS处理的细菌相比,从Cu@G-AMPs处理的细菌中鉴定出的DEPs,包括lytM、msaA、isaB、mecA和msrA,显著下调(图6d)。此外,当外源性ROS引起MRSA细胞内DNA或RNA损伤时,相关的修复系统可能被激活以维持细菌基因组的完整性。总之,Cu@G-AMPs通过破坏MRSA内的应激反应系统(包括群体感应调节、抗氧化酶、基因修复和重组)来实现抑菌功能。PRM
是一种灵敏度高、分辨率高、特异性强的蛋白质组学结果验证技术
[
48
]
。
本研究选择了3个与MRSA氧化应激功能相关的靶蛋白(aaa、mecA和msrA)用于PRM。选定了29个含有半胱氨酸(cysteine,
Cys
)残基的
DEPs
进行
PRM
测试,主要是因为活性氧很容易使多肽中的
Cys
残基氧化并将其转化为化学键,如
S-
谷胱甘肽、
S-
亚磺酸、
S-
磺酸、二硫键和
S-
次磺酸
[
49
]
。
总的来说,PRM中这些选定的DEPs的定量与无标记技术的结果相似(图6f)。即验证了无标签技术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03
MRSA感染皮肤的治疗
应用于体内的抗菌肽经常遇到复杂的微环境限制,如伤口液、蛋白酶和pH值
[
26
]
。因此,本研究通过小鼠创面耐药细菌感染模型和药物分组治疗策略进一步评估Cu@G-AMPs在体内的应用前景(图7a)。创面感染模型每只小鼠总治疗期为7 d。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各组创面面积均有明显的愈合缩小趋势(图7b)。与其他治疗组相比,Cu@G-AMPs和万古霉素(VAN)
治疗
5 d
后创面接近闭合(附件
A
图
S14
)。需要指出的是,抗菌肽
piscidins-3
体内环境的稳定性无法保证,因此
piscidins-3
在促进小鼠伤口愈合方面的贡献与
PBS
相比并没有表现出理论上的优势
[
2
]
。
重要的是,我们在第1天迅速评估了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的伤口的细菌密度,发现Cu@G-AMPs和VAN比其他药物具有更理想的抗菌活性(附件A中的图S15)。凝血、炎症、增殖和重塑是小鼠伤口愈合的必要阶段,这一过程主要涉及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炎症细胞、肥大细胞和间充质细胞[
50
]
。相应地,Cu@G-AMPs和VAN处理3 d的伤口H&E染色图像显示,与其他处理组相比,炎症细胞数量少,结缔组织疏松(图7c)。随后,在第7天,Cu@G-AMPs处理的伤口轮廓显示出更厚的肉芽组织和几乎完整的表面细胞,这表明Cu@G-AMPs具有多种功能,包括拉紧伤口边缘和稳定肉芽组织(图7c)。我们进一步用Masson染色法评价各组小鼠伤口愈合的实际进展,Masson染色可使胶原纤维变为蓝色,肌纤维变为红色。在第3天和第7天,Cu@G-AMPs处理过的创面出现了大片蓝色区域,表明Cu@G-AMPs抑制了不良肉芽的生长,促进了胶原纤维的增殖(图7d)。抗菌肽piscidins-3是一种来源于鱼皮肥大细胞分泌的免疫因子,这促使我们用Toluidine蓝染色检测小鼠伤口肥大细胞的浸润情况
[
10
]
。肥大细胞浸润是皮肤组织损伤和过敏反应的普遍信号
[
12
]
。在第
3天和第7天,Cu@G-AMPs处理的创面中没有明显浸润的肥大细胞,这表明Cu@G-AMPs具有与VAN相似的抗炎功能(图7e)。为了调查Cu@G-AMPs是否对动物有不良副作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监测了小鼠的体质量波动。体质量变化超过20%通常被用作发病率、痛苦和总体毒性的关键指标[
30
]
。幸运的是,在皮肤伤口愈合过程中未发现副作用(如肿胀、发红或瘙痒)或体内毒性(图7b~c,附件A中的图S16)。
Fig. 7. Treatment of Cu@G-AMPs on bacterial infectionwounds.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wound infection model establishment; (b)images of wound healing in the groups of treated mice; (c) H&E stainingimages of wounds in the group of treated mice (n= 5); (d) Masson staining images ofwounds in the group of treated mice (n= 5); (e) tolonium chloride stainingimages of wounds in group treated mice (n= 5).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analyzed using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s; **PP
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分析不同药物治疗小鼠创面中血小板内皮细胞粘附分子-1(CD31)和PCNA的含量。绿色荧光CD31和红色荧光PCNA是代表血管生成的一对常见标记物
[26]
。与其他治疗组相比,Cu@G-AMPs和VAN治疗3 d后创面出现了更多的CD31和PCNA(图2)。附件A中的S17和S18)。当第7天创面处于重塑期时,与其他处理组相比,Cu@G-AMPs和VAN处理组的样本中CD31和PCNA的含量较低(图S17和图S18)。也就是说,Cu@G-AMPs延续了抗菌肽的促血管生成特性。事实上,细菌伤口愈合的整个周期都伴随着炎症反应,这是各种正、负免疫因子调节平衡的结果[
51
]
。具体来说,IL-10作为一种多功能负调节因子,在机体中发挥拮抗炎症介质和下调炎症反应的作用[
50
]
。使用Cu@G-AMPs和VAN处理的样品组在3 d后IL-10水平低于其他处理组,在7 d后逆转(图8a)。IL-1β和TNF-α是机体免疫反应的典型的多功能正调节因子。使用Cu@G-AMPs和VAN处理的样品组在3 d后检测到的IL-1β和TNF-α水平高于其他处理组,在7 d后则相反(图8b~c)。基于这些结果,在药物治疗引起的不同愈合周期中,伤口免疫因子的实时释放存在差距。
Fig. 8.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infected wounds duringhealing. (a) IL-10 expression of wounds in the group of treated mice (n= 5); (b) IL-1β expression of wounds inthe group of treated mice (n= 5); (c) TNF-α expression of wounds inthe group of treated mice (n= 5).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analyzed using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s; **PP
结 论
受抗菌肽中铜镍结合基序的自然防御机制启发,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含有单原子Cu催化剂的人工抗菌肽复合物(Cu@G-AMPs),用于抗菌治疗。在鸟嘌呤掺杂丰富杂原子制备的底物上,以配位数为2、平均键长为1.91 Å的方式固定了单个Cu原子。Cu@G-AMPs表现出类似芬顿的催化活性,在应对MRSA时将产生并递送出致命的活性氧化物。这些ROS对MRSA的应激反应系统,包括群体感应调节、抗氧化酶以及MRSA内部的基因修复和重组,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值得注意的是,Cu@G-AMPs能够适应体内复杂的微环境,在耐药细菌感染的伤口区域显示出促闭合、稳定肉芽组织、促进胶原纤维增殖、减轻炎症和促进新生血管的现象。本研究设计的Cu@G-AMPs将为有效应对耐药细菌威胁提供新的视角。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eng.2024.09.021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查看原文。
专家介绍

汪少芸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
福州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院长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后,现担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福州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入选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省A类高层次人才、省高层次创新人才、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担任国家“一流专业”负责人、“生物与医药”博士点负责人、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 《Food Biomacromolecules》主编,《Food Frontiers》副主编,《Food Science of Animal Products》科学主编,《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Journal of Future Foods》、《食品科学》、《食品工业科技》和《福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编委,《中外食品技术》首批翻译专家。主持承担省部级以上及横向重大重点项目40余项,编写著作8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79 件,发表SCI/EI收录学术论文230篇,多篇论文获中国食品学会创新科技论文一等奖和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入选Elsevier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主持成果获国际食品功能因子(ICOFF)学术大会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食品产学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福建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均第1);获紫金科技创新奖、厦航奖教金奖;获评宝钢优秀教师、卢嘉锡优秀导师、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科技创新-杰出青年、省优秀教师、省最美科技特派员、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财经自媒体联盟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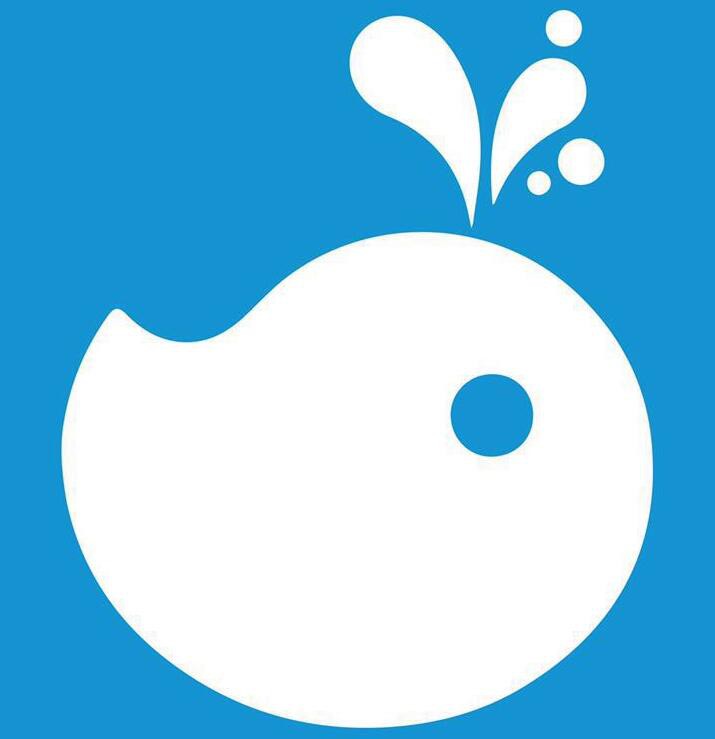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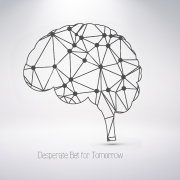






















 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贝壳财经视频
贝壳财经视频  尺度商业
尺度商业  财联社APP
财联社APP  量子位
量子位  财经网
财经网  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