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看理想
"
看理想App七周年,我们开启了一系列以“继续下去,就是可能”为主题的人物专访,邀请一些在各自领域“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分享这些年的故事、思考与信念。
第七期的嘉宾,是人类学者袁长庚老师,他也是看理想《倒霉人生生活指南》《工作与人生书单》节目的主讲人。
"
袁长庚老师的第一次出圈,是因为开设了一门名为“理解死亡”的课程,在课堂上,他甚至让同学们模拟自己策划葬礼。后面因为种种原因,这门课没有继续。
近些年袁老师的公共表达、对谈等等越来越多,甚至在抖音小红书自己开直播,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谈书,有时候谈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甚至会聊摇滚乐。

《留校联盟》
在很多人眼中,袁老师似乎特别擅长和年轻人对话,但并不是每一位学院里的知识人或知识分子在尝试走向更广阔的公共舆论场时,都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
在这次访谈中,袁老师说,今天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类似于“艺人”一般的自觉,是你需要建立连接,调整姿态,而不是要求听众来适应你。
来源 | 播客“看理想时刻”
采访 | dy
01.
年轻人那边,
不是你想站就能站过去的
我大概只能够触碰到中国的青年问题的一部分,当然做高校老师就会接触到青年群体,因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我是“自己努力”想站在青年这边,我就能站在这边的,因为这个群体太大,而且考虑到地域群体之间的差别的话,个体经验非常有限。
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职校生写作的这样一些作品密集地被出版了,职校生跟我们这种在大学里接触到的学生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自己还是比较慎重,好像我多么了解青年问题,或者是我在价值观上怎么选择了站在青年这边。
我只是在自己的生命处境里面比较忠实于我面对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它会和青年群体发生联系。但是我也并不认为我自己掌握了多少的资料,或者是说掌握多少的可能性。
02.
公众表达,
需要有“近身肉搏”的准备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以后,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面对的受众群体的复杂性大概是20年前没法想象的。
我是跟着中国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20年前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也是在上网,也是在冲浪,但我们小的时候的互联网,绝对是个精英文化,是不管在经济还是知识层面的少部分社会群体才能拥有的这样一种资源。
所以当然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那个时候所在的环境是相对而言跟你比较同频的,或者是至少是大家就算是争论,好像争论的也是比较严肃的事情。
今天说实话,不管是叫做受众,还是叫做对话的对象,还是所谓“你面前的这个人群”,都是一个庞大到你难以想象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比如在今天的算法机制下,你的言论或者是你的某种表达会被一些以前你难以触及到的群体看到,然后你可能就会遭到直接的冲击。
我觉得这是技术设施改变了以后,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空前的挑战。
以前,比如说我们就像上课一样,你的课堂上只有你的学生,只有你的同行,那个时候的对话状态是相对而言比较舒服的,而且你的安全感,你的直接反馈可能会相对而言更积极一些。
但现在等于说你站在街头,甚至站在菜场的入口,你的声音被听到的更多的可能性是可能跟你完全不同的一些群体,那么我们感觉到这个状态不理想,或者是有些沮丧,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
因为今天技术手段改变了以后,整个这个声场效应被改变了,那么不管是讲的人和还是听的人其实都觉得有点奇怪,所以这个大概也是人类在文明史上没太遭遇过的一些情况。
从好的方面讲,我们有些新的可能性;从坏的方面讲,它可能会让人和人在没有共识或者是没有一些必要的信任的基础上,直接地遭遇(彼此)。
所以今天是一个相对而言好像看上去比较轻快,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认为是比较廉价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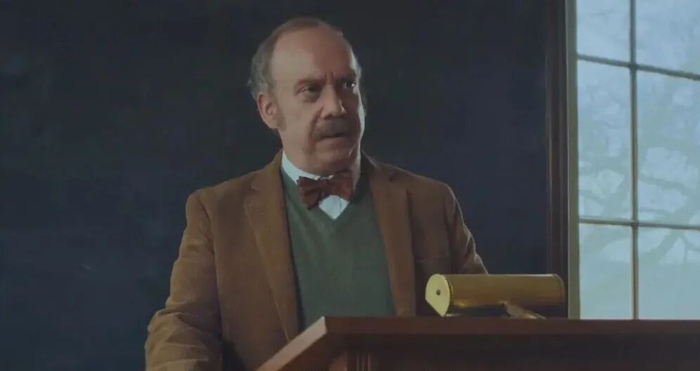
《留校联盟》
但是我置身看理想年会现场的时候,我还是在想一个问题——我想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假设比如说这个社会愿意听我跟成庆老师讲话的人就这么几千个人,以前我们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太没有意义了?因为人那么少。但是我现在更多想的是,你今天的表达或者你今天的工作质量,是不是对得起这几千个人?
我现在更在乎这个,意思是说,你自己真正的渎职或失职,不在于你没有去扩张你自己表达的那个边界,或者联系到更多的人,而是你的工作本身可能辜负了跟你真正走的比较近的一些人的他们的嘱托,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期待。
所以我现在不愿意过多去跟自己纠缠说,你到底有没有在传播,或者有没有在做得更广,我觉得能不能守住核心阵地可能都是今天的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就像我觉得你肯定不算是一个懈怠,或者说一个没有上进心、或者是对严肃知识没有兴趣的人,但是我今天其实每次面对像你们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找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抚慰ta的层面,也有一些给ta传递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新的视角?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实除了知识本身之外,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比如你对受众的理解,你对你自己所掌握的一套知识——因为理论上讲你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发生在昨天,那你自己像个使者一样——你有责任把它用一种新的形式带到今天,那你自己的后半部分工作是不是做完了?这个如果问下去有很多的可能性。
一方面,今天的危机确实是以前难以预料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危机当中大概还有一些比较核心性的工作还是在延续的。我自己现在反而比较关心这个核心的延续性的工作,我到底做得怎么样?或者是我有没有至少有没有让它跟我接受到的一些资源是匹配的。
03.
知识分子的表达、姿态转向
我们今天这种在公众讨论当中的这种态度或者是意见的对立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人”内部在互相伤害。
严格意义上讲,因为我们面对的一些可能共同的困境是更多的,但是大家现在确实又已经习惯了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方式去回应你所面对的——不管是别人给出来的意见,或者是可能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些表达。
这个很难讲是进步还是退步,从积极的面向而言,在面对权威,或者是面对一个你曾经可能认为你自己不太配跟他对话的人的时候,你大概今天可能有了底气,敢于表达了。

《留校联盟》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好像我们其实原本是可以有那种对话或者是理解的可能性,但是可能因为一些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我们所不可把控的一些要素,就会使得本该展开的一些对话没有能够展开。
我觉得这个分两说了,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一点:不管你的经济水平和掌握权力的多少,你肯定都是精英阶层。因为至少自己掌握了表达的主动性,掌握了表达的渠道和权利,这一点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理解,很多同行包括一些老师会觉得非常的委屈,怎么我就变成是一个首先需要被审视,甚至需要被质疑的这样一个对象?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结构下的不可避免的状况,我们自己在发言的过程当中要意识到你不可能跟所谓的普罗大众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你一定有些东西是相对而言比较漂浮在外层的,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意识,否则的话,过去这几十年什么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和知识分子本身反思,等于说没有做。
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老师可能相对而言,他的表态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
例如成庆老师、王芳老师,包括段志强老师,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自己的角色和处境本身就像是——我不知道用这样的比喻是不是有点残酷或者太夸张了——我们还在战火最核心的部分,我们还在看见人员在伤亡,我们看见人们是怎么受伤的、怎么挣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对现在人们受伤或者是倦怠,或者是有这种压抑体验的状态其实是更感同身受的。

《留校联盟》
虽然你真的要去讨论思想或者讨论文化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要求柏拉图怎么去下场到你今天这个时代说话。陈嘉映老师大概讲过同样的话,就是在柏拉图那个年代,你也不要问柏拉图为城邦做了什么,你应该问城邦为柏拉图做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从来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即便是在柏拉图那个年代,他也需要不断地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本身的诚意。严格讲起来的话,知识分子调整自己发言的姿态和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只不过我觉得其实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几代知识分子都享受到了一个时代红利。比如说以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大家在经历上升的这个时期,很多人会觉得传媒是重要的,或者公共议题是重要的,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有知识分子声音参与进来。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状况,它会让我们忽视了,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状态,需要搭建平台,需要在每一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去想你今天的表达或者是内容是不是需要做出调整?
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冒犯的话,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在走向公众的过程里其实跟艺人是有一点像的,你没有太多的豁免权,就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重要,所以我不会为你们做出改变,应该你们来适应我,或者你们应该来学习我做的这东西,这东西有多重要。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其实也需要调整一个基本的立场和发言的状态。当然我们在公共表达的过程中也都会有一些很沮丧的时刻,或者也都会遭受一些误解,也不是说我们(有这个态度了)就时时刻刻都在走向对话的过程里感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
但是这个就像是医生一样,你不能说我今天也希望来找我的病患本身都很愉悦,都面带微笑,我们春风和煦地进行这种讨论。那他就是在一个不舒适的状态,所以他会愁眉苦脸,他会心情不好,他会对你善意的表达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调整完了这个基本的预期之后,可能大概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耗。
04.
像UFO一样飘进来的学生
很多媒体朋友也问过我,对这种年轻人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大概我站上讲台第一天就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教人文通识的选修课,我们以前在学校里上选修课的时候,那是一个社交场合,因为选修课不在那个最核心的培养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基本上是要么冲着兴趣去,要么冲着话题去,或者有些人觉得这课好混,就会呼朋引伴的大家一起去上这个课。
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因为兴奋,提前20分钟就到了教室,在讲台上看大家一个一个进来。但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就是在我面前大概有40多个来自各个年级的学生,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背着书包、戴着耳机,静静地,像UFO一样飘进来,找到一个座位。
而且大家在一个双人课桌上坐下之后,别人就会默认旁边那个座位是不能坐了,如果是挤到那个地方去跟坐下的话,那就是个很冒犯的事情。
那一天对我的冲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我在幻想着回到一个我熟悉的这个场景,那种理想化的校园生活,但是我这个幻想第一节课就破灭了。

《留校联盟》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是很想弄明白到底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但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情——
我上大学那会,可能是中国文科最穷的一个时间。首先在高等教育体系里面,大家整体上能分的蛋糕就很小,那么文科能够拿到的就更少了,我得是上到研究生以后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茶歇。就是说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你比如说有很明确的资源竞争的机制。
所以客观上讲,我觉得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环境里面没有资源,所以其实老师也好,或者是说你周围的环境也好,是有心力去倾听你的想法、状态的。
我的求学的生涯里面有很多的夜晚,经常是一个老师被我拽着,课后或者是什么时候就被迫听我聊天。现在想想看那些聊天都非常幼稚,但是他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拒绝,老师们也愿意听我去谈这些事情。
但是客观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学校里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因为我们下了课基本上都是行色匆匆,因为你上完课以后有其他事情要做,有自己的生活、工作,有各种各样的考评的任务在等待着你。
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然后这个分工体系里面又有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竞争机制,等于说我们的老师也变成了这个 KPI 的考核对象,然后学生也变成考核对象。
所以今天大家的问题是,老师有老师需要应付的问题,学生有学生需要应付的问题。所以今天的学生在台下看台上老师的时候,他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是更强的。
比如说我,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应该每个星期在课外再抽出两个小时时间来,像谈心一样跟大家再消化一下课上所讲过的这些内容。但是今天在我们目前的高校体系里面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有心力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你所感受到的就是,我自己热情如火,带着对知识的憧憬进入到了这个学院体系当中来,我会发现老师离我很遥远,而且现代的学术本身有一套自己独立的术语或者说黑话体系,它也不会关注你是不是能够理解,或者说跟你的那种生命经验之间的距离是什么。
所以你觉得知识也很远,老师也很远,所以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在学院里面经受过训练的人,对这个体制有一种深刻的失望,甚至是带有一种愤怒。

《死亡诗社》
我觉得这特别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一些场景,就是你面对的是一个你都不知道敌人在哪、不知道应该控诉谁的那样一个状态,你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一个自己在运转的机器。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些事情是在发生变化的,或者说它不再像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样理所当然,所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说至少在你面对公众的时候,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姿态。因为确实有些东西已经运转了一段时间,而且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和这种创伤性的后果了。
05.
“你有没有在那些人的生命现场里面站过哪怕几分钟的时间”
今天的学生为什么压力大?因为你哪怕只是想成为一个学术上有所追求,然后能够继续往上走的人,你就是不能犯错,你就是要做好规划,你就是要很明确地研究这套游戏规则,然后去想说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它的需求。
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生活的条件或者原生家庭的这种购买力的角度而言,他们好像确实比我们当时要厚重一些。
但这些资源的边际效应是在递减的,就是你被举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选择的路径,或者说你可以争取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丰富,所以大家越来越往一些比较窄的赛道上去走。
我的很多学生在私下也跟我承认,疫情三年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中学、大学这个阶段,你人生还将将要展开的时候,你刚想要去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封控,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出去实习,去走出校门之类,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死亡诗社》
我这个年代的人,大家还比较相信个人奋斗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这种信念是有经验作为佐证的。很多人确实是好像“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状态,但是今天我觉得人在面对结构性的这个限制的时候,你能做的事情客观上讲是在收缩,或者说你自己能够掌握那个潜力是在下降。
所以这(年轻人的人生态度)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价值观上的讨论,或者是人生基本立场和姿态的讨论,但是事实上就是,你有没有在那些人的生命现场里面站过哪怕几分钟的时间?你真的从他们的角度接受一下这个迎面而来的这种冲击和压迫的时候,大概你也会至少保持沉默吧。
所以我自己现在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是,如果有些东西你自己也没法改变,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帮别人去缓解,那你就尽量少说风凉话。其实做一个比较轻佻的、外在的评论是很容易的,但是分担、共情这种事情是更难的。

看理想七周年特别访谈👇
各大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播客收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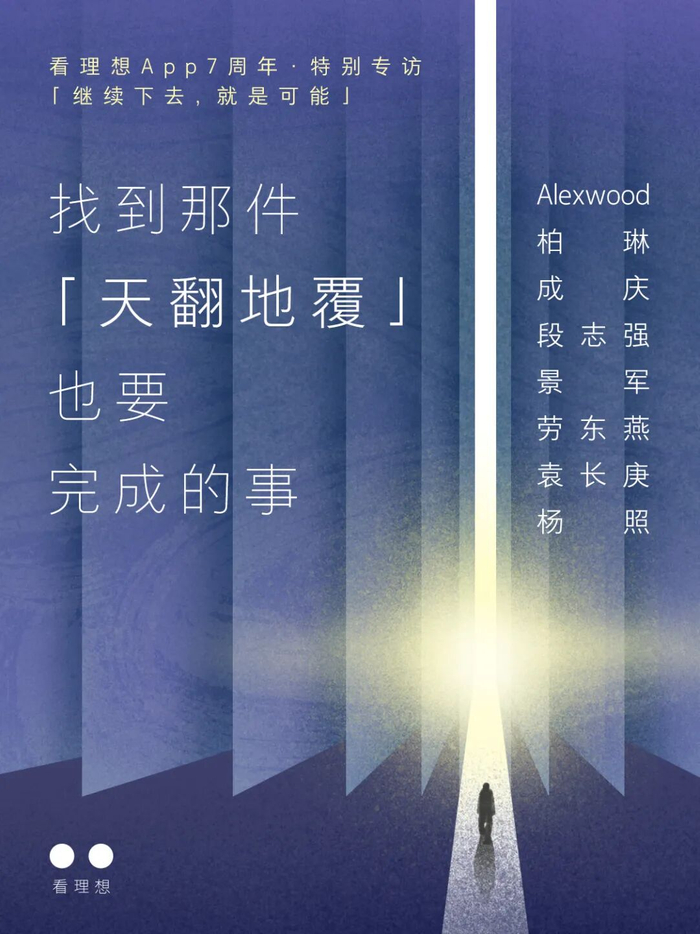

4001102288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