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出海,正在进入百舸争流的状态。
“当国内媒体广泛讨论当地文化给中国企业带来挑战的各种轰动新闻时,真正的一线管理者实际上从容得多。那些从外部看来令人揪心的事件,对当地管理者而言尽管并非轻松,但也并不轰动。”
林雪萍在其新书《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和突破》中如此写道。他当然有足够的底气这样说,因为这本书及其背后的观察,确是一部基于田野调查的中国企业出海纪实与产业分析。
作者林雪萍听取了100多家国内外工厂、200多位海外亲历者的倾诉和分析,来自一线鲜活的反馈让我们重新思考:出海的战略从哪儿开始设定?中国式高效率放在海外有效吗?投资是放诸四海皆受欢迎的吗?选择什么人做海外业务负责人?相比资金风险,文化鸿沟和认知短板这两个大出海上最大的拦路虎要凶悍得多……
这些颇为务实的话题或说课题,正是本书致力于探讨的:中国企业如何相对安全地“真出海”?本书提供了多元、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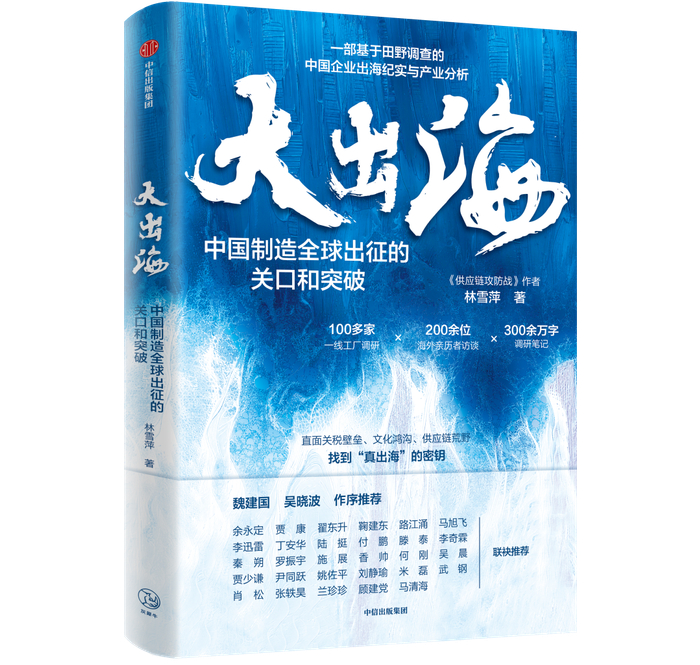
林雪萍
《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和突破》
以下主要内容摘自林雪萍《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和突破》。
中国企业大出海
当各个国家超市里的商品标签上越来越多地出现“Made in Vietnam”(越南制造)或者“Made in Turkey”(土耳其制造)的时候,商品生产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全球每个超市的商品都跟中国有关,变成全球每个新工厂都跟中国有关。中国工厂似乎突然出现在全球版图上,每个地理空间上都留下了中国企业家的身影。
这是一次群体性出海。中国制造业从未经历如此大密度的全球出征。行业包罗万象,从手机、电视到汽车、园林割草机等。
这也是一次仓促性出海。201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引发了大量代工厂的迁移。从2022年开始,中间零部件的工厂也开始加速移动。中国从“制造力为中心”到“设计力驱动”的切换周期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球制造业的洪流已经进入新的大峡谷。
对于多年关注全球制造业变迁的我而言,中国企业这次出海有一个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工厂”。一个工厂的迁移,带动了更多工厂移动的连锁反应。这些移动,引发了中国制造能力搬家的思考。
出海的话题,对中国企业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很多企业已经早早出海,成为国际化力量的一部分。那么这一次规模广泛的出海会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描述一个“工厂视角的出海”。
为了寻找答案,我开始大规模地寻找一切能够找到的中国海外的一线经营者,以及具备海外从业经验的人。在过去3年中,我调研过国内外100多家工厂,访谈了200余位海外亲历者,每天都沉浸在大量的对话与资料调研之中。
当访谈调研完成之后,我才发现不知不觉中已经涉及企业和机构大约300个。当积累了超过300万字的调研笔记之后,一个五彩缤纷而且与现实感知有着众多差异性的海底世界,像水族馆一样在我眼前逐渐展现。
当国内很多企业因关税大棒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些同行已经将其当成一次拓展全球业务的外部力量,反向形成一种驱动内部组织变革的力量。逆风而上的焦点,变成了“向上”,而不是“逆风”。

重构价值链
价值链是战略层面的考量,它决定了一个企业以何种方式来获取利润。这跟它在整个价值链条的环节有关。对于一级汽车供应商浙江均胜电子而言,它需要识别新的电子技术对于大众汽车的价值。只有在欧洲基地围绕汽车电子系统进行多元产品开发,才能确保它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只有将前后价值链打通,才能实现“战略出海”。
企业出海要获得持久的回报,就需要尝试改变价值链的组成部分。机器人公司南京埃斯顿在国内已经稳坐国产机器人的宝座,而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则以并购为主。被并购的海外品牌会加快与中国的供应链嫁接。在收购德国老牌焊接机器人公司克鲁斯、英国伺服电机公司翠欧之后,全球交互嫁接的行动就开始了。克鲁斯的技术实力雄厚,但产品种类却比较单一。埃斯顿借助南京研发设计密集的特点,为克鲁斯开发了新的机器人。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第一次在德国工厂制造来自中国设计的机器人。而为了丰富翠欧品牌的产品线,埃斯顿为翠欧开发了配套的运动控制器。这种交叉互补的方式,将中国激烈竞争的市场所形成的十足活力,注入海外老品牌之中。
中国企业的价值链空间正在向外延展,以满足全球地理空间的需要。按照不同地方的标准体系来设计产品,正在成为中国研发工程师的基本理念。这种改变,并不只是对中国企业而言。即使是落地中国的外资企业,也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转变进程中寻找新的机会。
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深度扎根中国的外企也会面临“再全球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双方借力、互相交织的过程。
金风是全球最大的风机制造商,高度重视国际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金风长期保持与海外科研机构的开放合作,以及和欧洲供应链的长期技术与订单合作。这不仅仅是商务合作,更是与全球技术发展潮流同频共振。金风跟德国弗兰德减速箱旗下的威能极有着长期的合作。后者不仅提供了可靠的齿轮箱,还可以从齿轮箱受力机构和部件磨损机理,为整机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分析视角。这种来自零部件企业的知识反哺,对中国主机制造商有着重要的意义。感知全球不同地域的实践经验,是技术升级的重要环节。

走进自己的无人区
中国制造能力的边界,还需要进行更好、更广泛的探索。而通过涉及改变价值链的节点,是企业最需要考虑的战略方向。
进军海外的产品不再只是模仿,而是独立定义独特产品,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进入这样的无人区。从企业生命周期看,这正是企业长大、成熟的成年礼,出海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调整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攀升到更高的价值空间,这正是一个企业如骨骼拔节成长的时代。
这些中国企业在国内持续提高制造能力,强化供应链能力,而在海外则致力于品牌多元化。品牌与供应链的共振,强化了企业在海外价值链的地位。
厘清贸易、品牌和供应链这三者关系的企业,会成为中国制造大出海的新玩家。在许多并不引人注目的垂直领域,这种三节鞭组合呈现了价值链要素重组之后的威力。
大出海需要一种新的供应链世界观,将全球能力节点化,然后重新组合,在一个更加柔性的组织中,寻找新的财富机会。以供应链为龙骨,中国制造新的力量也在形成。
中国工厂的能力可以在全球视角下重新被审视。供应链能力可以与品牌进行最大胆的结合。在美国、德国,到处都是丰富的小品牌,它们往往习惯于在本地活动。用全球化包围本地化,驾驭好这些小品牌,就可以借用中国供应链的旺盛能力。

位置改变价值
当一个企业的地理空间发生移动的时候,由于更加靠近用户端,企业也有更好的机会重新调整价值链。
出海并不只是向海外布局工厂,而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完成各种可能的能量交换。
实际上,“出海”并非只有一个向外的箭头,它也有价值向内的指向。德国技术与中国供应链能力的嫁接,正在产生新的生命活力。源自德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回头浪,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从总部管理到管理总部
总部容易将海外的战略风险看成细枝末节,而外派管理者容易高估总部对于本地的了解程度。双方的认知差天然就有扩大的倾向。外派管理者需要意识到,自己要不断努力去缩小这种认知差。“管理总部”,就需要具有引导总部理解当地的能力,向总部传递财务之外的更多信息。
外派管理者“管理总部”,就像是向上打开了天窗。总部能够充分了解本地现场的情况,外派管理者也能获取更多总部资源的支持。
海外并购出现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者。然而有一些公司娴熟地展示了驾驭跨国组织的能力。这些公司的并购时间都在10年以上,稳定的业务增长验证了这种组织设计的实用性。对于德国工业如此成熟的国家,直接派出一线经营者绝非良策。管理海外企业,并非一定跟总部进行文化对齐。用当地企业所习惯的方式去管理,中国企业的跨国运营不得不努力适应这一点。
林雪萍在书中说:在企业出海的各种挑战之中,最重要的挑战是来自认知的差异性。如果中国企业一味抱持着“效率优先”的理念在全球发展,那就会在很多地方碰到认知障碍墙。
你认同文中这些观察和观点吗?你所在的企业是否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大出海路径?有哪些宝贵经验和避坑指南?欢迎与我们分享,将机会获赠这本《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和突破》。



财经自媒体联盟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贝壳财经视频
贝壳财经视频  尺度商业
尺度商业  财联社APP
财联社APP  量子位
量子位  财经网
财经网  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