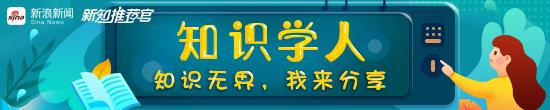


科技加速与“人工”挤出
前几日去朋友家玩,在他们小区门口体验了一个新业态——无人台球室。
注册会员,刷脸进入台球室。内部空间紧凑但舒适,灯光柔和,环境整洁,完全不似以往台球室的脏乱差和乌烟瘴气。
系统比较智能,扫码、开台、支付费用,对应球台上方的灯亮起,球台下方球盒的塑料盖板自动打开,将球取出就可以玩了。一小时只需38元,团购更优惠。时间一到,球进入球盒就取不出来,无法新开局。加上系统计时,十分高效。然后打开手机结账,关灯,走人即可。
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了解球台使用情况,不至于到了干等。也可以远程先支付费用占台。除了占台,还可以拼桌,两人均摊费用,或者三人分球模式(由“开灯者”付费),将日常打台球的各种场景都智能化了。
这里打球感受良好,氛围轻松,适于社交,来打球的也多是白领、年轻人,甚至女孩子偏多,因而生意火爆。以往,开设这么个小台球室,日常运营打理最少需要两三人,大城市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而且人工效率偏低,这个智能化台球室不得不说是一种商业成功。
当然,这个无人台球室的智能化系统并不复杂,与人工智能高科技差之甚远。但肉眼可见的是,数字化、人工智能化渗透效率越来越高,对人力的挤出日益明显——一个这样的台球室的智能化,抵消的就是两三个就业岗位。
以往,普罗大众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感受还不那么明显,譬如对程序员、设计师、文字工作等岗位的替代,以及AI写歌之类的时髦应用,毕竟这些岗位与普通人的生活有一定距离。
但随着数(数字化)智(人工智能)化的应用加速,譬如无人驾驶、无人零售、智能安防、智能物流,以及像这样的智能台球室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速渗透,大量像司机、店员、保安、分拣员之类的普通岗位,也在肉眼可见地消失。
科技的加速与“人工”的挤出,正呈现一个此长彼消的态势!

科技产业升级与城市内卷
人能与人工智能竞争吗?少部分科技从业者和高级专业技能者之外,普通人恐怕很难。道理很简单,人工智能的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聚合了海量“众人”的力量,超级理性且快速迭代,单独个体怎能竞争得过?
因此,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人工智能对“人工”的淘汰才刚刚开始。未来,“人工”将越来越不值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怎么办?只能不断地卷自己。
这就关乎一个现象,即“城市现代化陷阱”——当然,这个词算是个人“发明”,纯属个人观点,但有必要梳理一下,以供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发展趋势。
人类几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本质围绕着“城市+工业+商业”,即城市工商业发展。城市是资源和人口聚集的结果,聚集产生规模、分工效益,但也推高城市成本,譬如政府的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市民的住房、教育、生活成本等。
随着城市各项成本水涨船高,就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以选择更能承担相应成本的产业和人口——主要是科技+资本相关产业、企业或人才。显然,掌握科技+资本核心能力的企业和人才注定是少数,他们会越来越值钱,而大多数人越来越不值钱,不断被城市挤出。普通人为了维持住城市的基本体面,怎么办?只能卷自己——这就是多数人内卷的本质。
那么,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未来城市内卷会好转吗?大概率不会!随着科技迭代加速,内卷还将趋势性地加强。因此,经济与社会如何发展,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科技创新”,就能回答。
以东京为例,这是我认为堪称城市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这里经济发达,GDP占全日本四分之一,人口密度则是北京的5倍,但基础设施完善,城市井然有序,人人彬彬有礼,治理优秀。而且到处都很干净,十年前,我们去参观过东京市中心的建筑工地,几栋在建的大楼被绿幕包裹得严严实实,现场施工管理十分先进,竟然看不到一点灰尘,也几乎听不到什么噪音,让我们都惊讶得张大嘴巴——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
但另一面,东京(以及韩国首尔)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据说在东京,平均每天都会有一个人卧轨自杀,而富士山北麓的“青木原树海”,每年都有数百人跑进去自杀,被日本人称为“自杀森林”,更不用说越来越普遍的抑郁症。

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崇尚公共秩序的东亚内倾型文化地区,叠加科技产业升级,城市的内卷化就是社会发展之必然。

人类的反科技思潮
虽然在中国当前主流语境下,反科学、反科技几乎与“反动”“倒退”“蒙昧”相挂钩,但需知,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反科学”“反科技”思潮或运动始终与科技大发展相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就掀起过一阵“反技术主义”文化思潮,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英国作家爱尔德斯·赫胥黎、艺术家卓别林等。
他们主要从两方面批判技术发展:一是从生态学观点抨击技术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力;二是从人道主义观点抨击技术正在日益失去人性,譬如卓别林就在多部电影中表现了大工厂流水生产线没有人情味的情况。
后来,西方社会对科技发展形成了“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两种论调。哲学家海德格尔一般被认为是技术批判者和技术悲观主义的代表,1946年他在其《形而上学之克服》里就提出,“计算和规划战胜了所有的动物性,人成为最重要的原料”。
他认为,技术的本质首先是把“存在”变成了某种可认识的对象、可理解的“存在者”,然后征服和控制它,如此,人的生存世界就没有了任何神秘性,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的来源。
二战尾声,原子弹爆炸更冲击着世人的神经,白光一闪间20万人化为灰烬,彻底震碎了许多人的世界观,并引发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集体反思,“科技发展下去将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逐渐成为流行观点。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目睹了自己制造的产品的灾难性破坏之后,开始转向说服美国政府停止和限制核武器研究。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认为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并没有增加全人类的福祉,而是给整个文明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被杜鲁门嘲笑为“crybaby(爱哭鬼)”。
50年代,美国兴起一场名为“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运动,主要目的是打击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和叛徒,连带着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成为打压对象,奥本海默就牵连其中。在当时的氛围下,许多政治人物还热衷公开嘲讽知识分子的“智识”来博取选票,随之由政治而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矛盾不断激化。
事实只是政治人物和民众“反智”这么简单吗?并非如此,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后发现,美国社会中的人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愿意接受“智识”,民众对脱离他们实际生活的“智识”有一种反叛、不信任和敌视。“反智主义”其实是一种传统,据此,他写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
60年代,一种新的“反智主义”在全球智识的高地——美国大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反理性、愤怒的一代青年,对高等教育体系中功利主义和学术等级制度发起反抗,促成了嬉皮士运动的兴起,并夹杂着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催生了“咆哮的6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唾手可得,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智主义”式微,社会反而进入了拉塞尔· 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说的“片刻思考、即刻评论”的时代:人们对知识分子逐渐退居象牙塔、闭门造车深恶痛绝,对他们充满攻击,像我们的互联网对“砖家”的嘲讽一样,“智识”反而受到更多挑战。网络社交化后,反智主义更多走向民众和政治,民众对社会分化、贫富悬殊日益不满,对体制和政府的不信任加剧,助推反智主义愈演愈烈,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的上台、民粹主义的兴起、疫情反噬等,就是代表。
所以,“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有着漫长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的结尾写到,“对这种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没有持续走低,也没有突然下降,而是经受着周期性的波动”。而这本书的封面赫然写着——反智,不仅是美国的偏见,其实也是全世界的隐疾。
正如一位家庭妇女的抱怨:“我希望AI可以帮我洗衣服洗碗,这样我可以有时间来搞艺术或写作,而不是AI代替我搞写作和艺术,我来洗碗洗衣服”,工业化将人物化,数字化将人算死,人工智能将人挤出……当前科技发展的走势,难免不引发人类的“反科技”反思。


人工智能与“人工”的平衡
ChatGPT带火的人工智能技术,无疑是当前全球科技热点。对此,美国社会却一直充满矛盾情绪,反对者和政府、企业的强力推动并存。其中,反对者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他是OpenAI早期的赞助者,却多次在公共场合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威胁,尤其是国家之间在该领域的军备竞赛,恐怕最终将人类卷入人工智能的世界大战之中。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多次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的忧虑,并提出以税收方式缓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冲击的确在加快。笔者之前从事过广告业,最近了解下来,大多数朋友的广告公司员工越来越少,很多只剩下个位数。尤其是一线城市,招一个设计师、文案或策划师的工资和五险一金的成本太高,而广告费还在不断下降,越来越多老板日益转向AI,尤其是广告费给得不多的客户。AI做出来的图,写出来的文案、方案,虽有一定痕迹,但一般情况下都能及格,而且做得越来越好。回望过去,广告这个行业也养活了不少城市中产,以后怕是不行了。而类似这样曾批量诞生城市中产,未来却面临被全面替代的行业,其实非常多。
甚至连好莱坞的导演和演员们也坐不住了,2023年7月,AI发展如火如荼,却迎来了好莱坞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的联手罢工反抗……虽说,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创造一些就业岗位,但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恐远低于其冲击的就业。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科技,将导致市场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低,而全球人口已突破80亿,还在往百亿大关发展。“人”与市场的供需逆转,未来会不会导致AI对人口的“抑制”?
当然,从社会实际发展的角度,坐而论道讨论技术悲观还是乐观,意义并不大,科技的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也是必须。我们要谈论的:
一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物质发展的目的,终究是人,而不是更多的经济和物;
二是,努力实现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社会发展与社会分配的平衡——譬如,发展最快的人工智能科技,与普通人生存所需的“人工”的平衡。
科技不仅要以市场为导向,也需要与社会、民生更好地融合。这并非“反科学”、反对进步,而是摆在眼门前的现实所迫,和校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